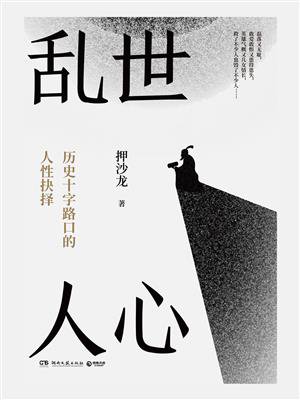四
司马迁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之际。在理智上,他拥护大汉帝国,认为它带来了秩序和繁荣;但是在情感上,他更偏爱旧时代的精神。他喜欢那种张扬,那种独立,那种自由。而在他之后的史家,对旧时代的精神越来越隔膜,也越来越不接受。
班固就很不喜欢那种张扬肆意的劲头。他评价司马迁的时候,一面推崇他的才华,一面对他进行价值观上的贬斥,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那么他写的《汉书》又是什么样子呢?郑樵在《通志》里把班固骂得一钱不值,说拿他和司马迁比,就像拿猪去和龙比一样。这当然是骂大街式的偏激,不可置信。其实《汉书》写得端严谨饬,文字硬朗干练,别有一种好法。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汉书》之于《史记》,有点像修昔底德之于希罗多德,前者脑子里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的兴衰,后者脑子里却装着整个已知世界。
当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兴趣窄了,固然呆板但容易聚焦;兴趣泛了,固然灵动但也容易散漫,有时候确实很难两全。
把文字风格放在一边,单说观念,《史记》和《汉书》也迥然不同。比如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不过他所说的“游侠”,不是郭靖、萧峰那种侠客,而更像上海滩的杜月笙。这些“游侠”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公权力有一种隐隐的对抗。司马迁对此很欣赏,称赞他们言必行,行必果,诺必诚,感慨道:“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可班固就很厌恶这些人物。
他也写了一篇《游侠传》,批评里面的有些人表面仁慈谦逊,其实内心恶毒嗜杀。班固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真相,倒是司马迁把“游侠”给浪漫化了。但是班固讨厌游侠们,倒不是因为他们人品有问题,而是在价值观上就拒斥他们。他说这些人“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不守老百姓的本分;而且最可恶的是,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所以罪不容诛。
对照这两篇“游侠”,就能看到主流观念的变迁,看到帝国时代的降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史记》既是对新时代的预示,也是对旧时代的挽歌。后来的史家不管如何仰慕司马迁,实际上却不约而同站在了班固的立场上。司马迁和他笔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史记》里那种刚健质拙的精神也没有彻底消亡,它仍然潜伏在社会之中,只不过被挤到了比较边缘的位置。这种精神有好的一面,它召唤着人们的雄武之气,也召唤着个体的独立意识。在主流话语无所不在的笼罩中,它给人挖开一个可供自由呼吸的缝隙。
当然,它也是野性的,有时候甚至是暴戾的,是恃强凌弱的。它是“情义”对道德的无视,血性对逻辑的无视,私域对公域的无视。任何文明走向成熟的时候,都会打压这种精神。从本质上来说,文明是一种驯化,而这种精神就是它的驯化对象之一。只不过,这是用什么样的力量去驯化这种精神?又要把它驯化到什么程度?
《汉书》之后的正史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用大一统帝国的力量,把它渐渐驯化到温良乖巧的程度。司马迁已经窥见到了这个过程。对此,想必他一定是心怀不满的。《史记·列传第一》就是《伯夷列传》。在这个故事里存在着一种悖论,伯夷、叔齐相信君权的绝对性,因此反对武王伐纣;但是他们又否认君权的绝对性,所以又选择了躲进首阳山。这种糊涂而又矛盾的想法,司马迁未必赞成,但他还是郑重其事地写下《伯夷列传》,还放到“七十列传”之首,又是为什么呢?可能,他不见得欣赏伯夷、叔齐的观念,但欣赏他们的决绝。
是啊,天无二日,那又怎么样?民无二主,那又怎么样?你布下了笼罩一切的巨网,那又怎么样?我依旧可以拒绝你。他们都说天下的粟米都是你的,那么我一口都不吃,和你两不相欠。
然后,我可以自由地反对你。
是不是想多了呢?也许吧。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司马迁写下这篇列传的时候,心头燃烧着一股愤恨。他赞美伯夷、叔齐,多半也是因为这两个迂腐固执的老头子,做到了司马迁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