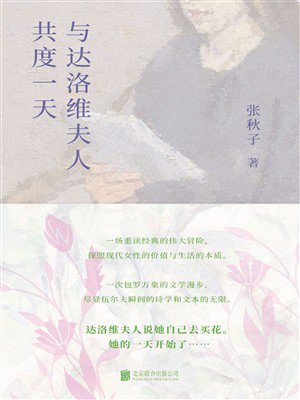3
设想这么一个场景:
一名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过活,大女儿乖巧懂事,二女儿则不受待见,母亲怎么也喜欢不起二女儿来。这天,早餐时分,三个人围坐在餐桌边吃饭,二女儿开始吃自己的那份面包:
从自己那杯牛奶里,把浸泡过的长长的一条黄油吐司硬皮捞出来,牛奶还在往下滴,就拎向她伸出的嘴巴。
(孙仲旭译)
读者可以试着猜一下,这一幕是从谁的眼睛看到的,又带着什么样的情感。我认为这是母亲看到的,她看得那么细,是因为她嫌恶得那么深。也就是说,小说家不需要写太多解释性的废话——“母亲带着厌恶的眼光看着二女儿吃面包,狼狈邋遢的模样让她感到恶心”——只需单纯地把场景本身写出来,就足以让读者感觉到人物之间的情感状态。这个场景,来自理查德·耶茨的《复活节游行》。耶茨之所以相信读者肯定能领会该场景背后的情感,是因为他深谙:目光是沉重的,他人的目光往往带有强烈的判断,它甚至比语言和动作更有力。比如说你在地铁里看到一个大汉在开着公放听云南山歌,手里还捧着韭菜合子吃,你想上前喝止又怕打不过对方,就会选择用目光冷冷地凝视和审判他。也正因为人们觉察到他人的目光是带有评价的,所以“你瞅啥”才会变成一句不满的回击。
在本细读章节中,克拉丽莎生命中的重力不仅体现在她对庸常生活的最终选择,也在于她自愿背负了他人沉重的目光。别人的目光构成了她生活的意义乃至重力。说白了,她总是活给别人看。
当她遇到休时,她用休的眼睛来自我打量,“莫名其妙地想到自己的帽子,兴许不适合清晨戴吧”;她渴望在走进屋子时,“人们一见她进来就高兴啊”;甚至,她幻想自己有某夫人的外貌、某某夫人的举止,因为她的容颜正好相反。
他人的目光总是饱含着深切的道德或者审美判断。
我曾看到孙隆基的一个妙论,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重视吃的民族,所有的感受几乎都可以用饱含口欲色彩的“吃”来言说,吃不消、吃力、吃苦、大吃一惊、吃紧、吃水线等等。我觉得把口欲之“吃”换成目欲之“看”,好像也是成立的,看轻、看扁、看重、看淡、看破、看不下去、看中、看好、看齐、看跌……反正,看这个动作,总是与被看之物建立起一种充斥着审美、情感、价值的复杂认知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往往是不平衡的,被看的那一方要么就是被抽去了价值,变得轻了、扁了、跌了,要么就是被赋予了价值,变得重了、符合心意了、值得期待了。两股力量始终在看与被看者之间博弈。有时候,下课后会有女生跑来跟我聊天,说自己今天很开心,终于鼓起勇气穿了露脐装,虽然会露出肚子上的肉肉;还会有女生和我说今天来教室里没有刮腿毛,就这么来了,感觉很自在……当她们这么描述自己的时候,我感觉到她们在努力和另一种牵引力量较量,和那种社会公认的什么才算是“美”的话语权力较量。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塑造性的力量,它出现在别人对你的打量中,传递的则是一套“白瘦幼才是美”或者“进行体毛管理才是美”的整齐划一的观念。
布罗茨基有个特别迷人的概念叫作“小于一”,谈的正是对社会把人塑造成整齐划一的力量的拒绝。每当步调一致的命令出现时,他就想躲在“自我”那个小小的躯壳里,永不停歇地观察着四周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个小小的我,比社会要求的统一的“我”要小,却永远不变,时间的流逝不会将其耗损分毫。对于克拉丽莎来说,她的存在则可能是“大于一”的,是重力过载的,因为那个小小的我太过于游移不定,所以只能用各种关于自己的幻想与来自他人的目光往上加码,几乎使她不堪重负。于是,她开始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自欺:
一旦结了婚,在同一所屋子里朝夕相处,夫妻之间必须有点儿自由,有点儿自主权。这,理查德给了她,她也满足了理查德。
我们的同学在读这句话时几乎都被骗过了,他们认为克拉丽莎获得了理想又松弛的婚姻。其实我头几次读时,也以为这句话是伍尔夫本人婚姻状态的投射,甚至引用过不少描述这对夫妻情感的资料来进行解释。后来我再反复读这句话,才觉察到里面一丝无可奈何的自欺,当我们无法得到真正渴望的亲密情感时,会退一步称之为“有点自主权”,就像人不得不妥协时,他会告诉自己这是“成长”。所以,紧接着这句话,伍尔夫又写道:“譬如,他今天上午在哪儿?在什么委员会吧,她从不过问。”亲密关系中的疏离与彼此不理解,被克拉丽莎的自欺包装成了一种相敬如宾。因为,这样的婚姻才能在其他人眼中获得尊敬。

自欺者往往需要包装才能自我说服。
在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笔下,自欺者用的道具是一个纸灯罩。名作《欲望号街车》中,已经破产并且滥交的南方淑女来投靠妹妹,妹妹此时已经嫁了一个粗俗的米兰人。姐姐始终摆出一副对粗俗无法忍受的态度,她每天都洗澡换衣服,还把妹夫称为没有被文明洗礼过的原始人,这些行为能够帮她建立良好的自欺幻觉,仿佛还活在有着廊柱的南方庄园中,一位富有的绅士终将把她娶走。但是,威廉斯特别残忍地用一个细节揭穿了姐姐:纸灯罩。布兰琪讨厌光秃秃的灯泡直射光芒,觉得没有美感,像妹夫家一样粗俗,所以她要求为灯泡装上一个纸灯笼作为罩子:
我从来都不够坚强也不大能自立。当你不够强的时候——软弱的人就必须得光彩照人——你就必须得披上软弱的亮彩,就像蝴蝶的翅膀,还得在灯泡上罩上个纸灯笼……
(冯涛译)
纸灯罩让人想到什么呢?
易碎的、脆弱的、不堪一击、幻影般的……在戏剧结尾,当姐姐的自欺与骗人被揭穿后,妹夫发现她无依无靠,就把她强奸了。在此之前,他做了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动作:把纸灯罩扯了下来,好看清姐姐的脸。请注意,这里再次出现了残酷的目光,撕下灯罩的目的,是要把自欺的姐姐看个清楚,揭发出赤裸的真相。姐姐的悲剧在于她为了迎合他人的目光而自我包装,但最后也毁于他人的目光中。实际上,在司汤达和詹姆斯的心理小说以及易卜生和奥尼尔的戏剧中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自我理解没有充分与外在世界的动态达成一致。比如,剧中人觉得自己幽默大方、广结善缘,其实则是众叛亲离,又或者,剧中人认为自己总是为别人着想,但其他人的反应则恰恰相反。
显然,好的文学作品会提供一种观看的参差感,就像天文学中所谓的“视差”,也即从保持一定距离的两个点观察同一个目标时所产生的方向差异。在文学中,这些视角互不兼容,不可化约,动摇了一个人的自足假象。
在这个细读章节中,伍尔夫并没有一味地把克拉丽莎塑造成一个彻底活在别人眼中的愚蠢角色,她也试图提供一种“视差”,用来纠正克拉丽莎被目光重力牵引的身姿。所以,每当她不由自主地倒向别人的目光时,伍尔夫就要颇为残酷地为她补上另一种纠正的目光,似乎要把她的失衡拉回中轴。克拉丽莎对自己的回忆是“十八岁的姑娘”,仿佛是永远的少女,但通过一个朋友的描述,她被残酷地呈现为“五十出头”的女人,带一点鸟儿的气质,花店里已经“见老”的皮姆小姐则第二次从他者的视角提示着她的衰老;当她幻想自己在晚宴上会如何珠光宝气、大放异彩时,彼得却又在一次次争论中,批评她只是一个楼梯顶上迎宾的俗妇。这样一来,伍尔夫就保证了克拉丽莎身上有反思、自观与顿悟的可能,她也因此会有下面的烦恼:
她多么渴望使人们一见她进来就高兴啊!克拉丽莎这样思忖着,又转身折回邦德街。她心里又泛起烦恼,因为做一件事非得为他人是愚蠢的。
克拉丽莎处于一种摇摆的状态中,宿命的重力和他人的目光拉扯着她倒向一侧,不甘与忽然闪现的反思又试图将她掰回来一些。于是,在整部小说中她始终处于顿悟的边缘,那顿悟如风中之烛,忽明忽暗,却从未真正照亮过整间屋子,甚至在赛普蒂默斯死时依然如此。出于同情之理解,伍尔夫不愿像神一样蹲在人物头顶沉思,而是以一种旁观的方式,从生活中借来一个原型——克拉丽莎这个形象与伍尔夫儿时的朋友凯蒂(Kitty Maxse)非常相似
 ——让其在小说中获得一种美学的膨胀与复杂性,进而邀请读者用个性化的阅读称量这个人物性命中的重力。至于克拉丽莎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你自己说了算。
——让其在小说中获得一种美学的膨胀与复杂性,进而邀请读者用个性化的阅读称量这个人物性命中的重力。至于克拉丽莎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你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