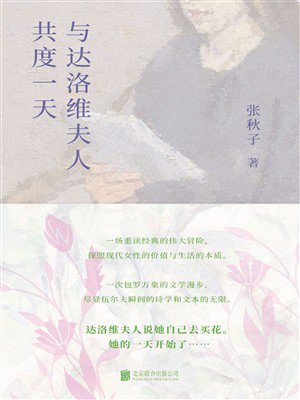4
文学技术也有其重力。
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蓝色圆点。请大家尽情地去幻想凝视这个圆点时脑中冒出来的东西,然后用关键词的方式速记下来。我从同学那里得到了如下内容:
一个蓝色的圆地球从井里看到的天空一张蓝色的膏药卫生巾的广告一倒水就会变成蓝色这个圆球呼应着桌面的蓝色如果是绘画我会把这个圆分析为它在呼应这个环境里的蓝色它是独立在泛黄墙壁之外的悬浮在这个温暖的环境里只能听到教室之外微弱的喧闹声感觉到自己的手因为热水而温热
或者:
一首歌太阳可以是蓝色的吗?爱伦·坡《红死病的假面》——蓝色的窗户很喜欢的颜色有一部电影《圆圈》昨晚看了一部叫《超脱》的电影眼泪也可能是蓝色的吧我在落笔的时候,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手机屏幕闪了一下到这里,可能你已经会心一笑了——我们在模仿伍尔夫的名篇《墙上的斑点》。文章的开篇,伍尔夫这样写道:
“大约是在今年一月中旬,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斑点。”整篇文章,正是在呈现由这块斑点引发的各种思绪。只不过,当同学们在捕捉自己脑海中的思绪时,可能早已忘记高中学过的这篇散文,毕竟,让中学生去“学习”意识流这个概念,并不是什么可供消遣的活儿。此时,他们虽然答不出对于“意识流”的各种学术性的定义与概念溯源,但他们已经在实践和感受这种写法。
由此,我们会发现几个特点:首先,意识的内容往往是跟个人的经验相关的,是具体的。如果你正好在读罗翔的《圆圈正义》或者正好看了一部电影《圆圈》,那么你的意识会很快找到附着点。现象学会把这称之为“意向性”,也就是人们的意识总得关于什么——aboutsomething——脑中一片澄明反而是需要训练的。用伍尔夫自己的话来说,心灵所接纳的万千印象犹如“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但是簇射总是有靶心的;而且,这个念头与那个念头之间的跳跃并不是全然无稽的,它们之间可能暗含着一种勾连。比如你先是想起了高中时读过的《墙上的斑点》,进而想到那是高中时难得的闲暇时光,继而自问,现在会比高中时调节负面情绪的能力强吗?一种暗中的严密逻辑将不同的念头勾连起来。最后,大家也都承认,我们无法把所有思绪全部抓住和写下,当开始写关键词时,总有一些念头溜掉、消失了,而写下的内容多少有点刻意创造乃至编造的味道。
其实,这就是意识流文学的特点——我们无须搬出任何权威的定义,只需感受自己创作时的状态。它的核心是人的经验,虽然套上了一种看似玄虚的思绪外壳。也就是说,每个人具体的经验构成了各自飘散的思绪的地基与重力,无论你的思维飘到哪儿,你都会被自己经历过的事所牵引。
在这个细读部分中,伍尔夫对克拉丽莎意识的塑造很大程度上调动的正是她自己的人生经验。人们经常引用她在塔兰别墅(Talland House)醒来时的回忆,那是她家在康沃尔郡圣艾夫斯的避暑别墅。午夜梦回,她总是能“听到海浪拍击,一、二、一、二,一阵浪花被送到岸边;然后又是浪花拍击,一、二、一、二,在黄色百叶窗后面”。这段个人经验对伍尔夫极为重要,因为在《雅各的房间》《到灯塔去》等作品中,它被反复书写,投射到不同的人物身上。因而,小说中露西推开窗后,克拉丽莎想到的是:“空气那么清新,仿佛为了让海滩上的孩子们享受似的”,而在接下来的思绪联想中,她想到的又是“波浪拍击,或如浪花轻拂”。
学生们自己的意识流创作也表明,两段看似无关的意识流之间也总有一枚小钩子将其勾连。有时候,钩子是相似的动作,有时候则是相似的词语,大家常说“××事勾起了我的回忆”,而不是说“黏起”“抓起”或者“抱起”,其实也是在谈记忆流动之间的微妙逻辑。露西打开窗子时推开铰链时的声音,继而引发了下一段中克拉丽莎对布尔顿的回忆,那时她也曾推开窗子,铰链作响,面朝大海。她不由得感慨“多么痛快啊”(whata plunge!),请注意,相似的动作与词汇出现在小说结尾处,赛普蒂默斯自杀时也是打开窗子,纵身一跃,完成了自杀。伍尔夫用“flung”(猛投、猛地移动之意)来形容他的自杀:“一面拼出浑身劲儿,纵身一跃(flung himself vigorously)。”plunge与flung不仅发音相似,意思也都指向“猛冲”“猛投”“突然跌落”。于是,开篇的达洛维夫人似乎无意识地对结尾的赛普蒂默斯发出了轻轻的叹息——这是怎样的纵身一跃啊!从一开始,伍尔夫就打定主意用同一个词把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人的命运对照起来,他们在生活表面的轨迹各不相同,但生命的重力却勾勒出他们共同的命脉。
意识流自有其重力所在,作家们对经验与逻辑的倚重其实仍然具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只是他们把控制的力量藏在了更深的地方,让读者产生了散漫无序、漫无边际的错觉。对文本的彻底解缚要再往后几十年才能在一些实验性质的作品中看到。比如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创立的“自动写作”。在创作之前,他会把纸剪成足够打字机用的长条,然后把它们粘成一个长达三四十米的纸卷,以便让他不间断地写作——或者说仅仅是自动地打字。打出来的内容很多时候是不可读的,完全抛弃了计划性,长长的纸卷就像一个塞满阴影的河谷,上面的字符则是无法辨清的地表植物。比如在《荒凉天使》的第三十七章,有这样的句子:
谁为何写下谁为何等待嗅事物IIIIIIIIIIIII O MODIIGRAGA NA PA RA TO MA NICO SA PA RI MA TO MA NA PA SHOOOOOOO BIZA RIIII…………IO O O O……M M M……SO—SO—SO—SO—SO—SO—SO—SO—SO—SO—SO—SO—
(娅子译)
你简直可以相信它们是猫在打字机上留下的随机的脚印,要么就是作家在嗑了药以后的幻觉中写作。
凯鲁亚克彻底放弃了跟读者讲个故事的愿望,他甚至都不想跟你好好讲话!眼睛滑过这个段落,故事的逻辑与文字的意义被彻底驱逐了,文字以符号的形态疯狂无序地流淌,甚至带有一丝温度和哆嗦感,那是刚从大脑里挤出来时还带着的体温的余热与肌肉的动态。相比之下伍尔夫的意识流就显得拘谨和传统得多:从创作意图来说,她依然在费尽心思跟读者讲故事,与荷马或者塞万提斯并没有不同。实际上,很多早期的现代主义小说都像一颗酒心巧克力,表里的口味和质地都是矛盾的。福克纳、乔伊斯也差不多,叙事技巧跑到了观念前面,故事讲得花团锦簇、新意迭出,但内核仍是一颗保守古老的温柔之心。

《达洛维夫人》带有传统小说的精心布局感和建筑般的设计意图:每一个思绪不仅要和下一个思绪暗中关联,还要草蛇灰线地伏延到小说的中部和后部,甚至,所有奔腾的思绪都要获得一个整体性的隐喻:达洛维夫人穿过的闹哄哄的城市、一条条喧嚣与川流不息的街道,不正象征着一个思绪翻涌不休的大脑?她根本就是在颅内漫步!
甚至,连小说开场的季节也经过了精心设计,伍尔夫把她的重力之锤放置在了盛夏六月。
六月,战争结束,街头忙乱,这是伍尔夫非常关注的月份。在日记里,她把盛夏的六、七、八三个月形容为一个“破碎的瓷器橱柜”,里面有太多碎片与变形。小说写到此时伦敦街头的躁动:“川流不息的马车、汽车、公共汽车和运货车;胸前背上挂着广告牌的人们(时而蹒跚,时而大摇大摆);铜管乐队、手摇风琴的乐声;一片喜洋洋的气氛,叮当的铃声,头顶上飞机发出奇异的尖啸声——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遍布强烈光线、热量、尘嚣的世界,也更会让人心绪烦乱、大脑充血。
为什么要强调盛夏高温这个细节呢?
小说中的温度与湿度都是读者在细读时可以留意的细节。温度的升高可能与小说中人物内在的紧张感有关,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正是在太阳高悬、热浪逼人的时刻,心烦意乱地拔出抢来,杀死了一个陌生的阿拉伯人。相反,冷使人向内蜷缩,削减语言,甚至冻结思绪。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塑造了严寒的俄罗斯冬日世界。小说开篇,两个年轻的中学生目睹了一场未遂的自杀,又讨论起刚见到的跟自杀有关的人和事,如此严峻的时刻,他们却觉得听不懂对方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将其解释为“天太冷,谈话很困难”。温度与湿度会从犄角旮旯里提供对小说核心象征与走势的提示,在《达洛维夫人》中,后文赛普蒂默斯的自杀其实在高温的天气中也获得了暗示。
而且,夏天这个意象在“一战”之后别有深意。“一战”的持续时间是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所以,人们常常把1914年的6月称为“欧洲最后的夏天”。在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里,四处充满了音乐与聚会,海滩、花园、客厅里留下了大量的欢声笑语。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以充满温情的笔调回忆了这个夏天:
1914年的夏天也仍然令人难以忘怀。我很少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夏天,比以往的任何夏天都美丽、繁盛,我几乎想说,更是夏天。连续多日,天空像蓝色的丝绸一般舒展,空气柔软而温热;草地暖暖地散发着幽香;树林郁郁葱葱,到处都是新绿。至今,当我一说出“夏天”这个词,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的灿烂七月天。
(吴秀杰译)
在伍尔夫笔下,“一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夏天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从前,欢声笑语回来了,街头熙熙攘攘,“这一切总算过去了”。真的如此吗?请注意,当作家交代“这一切总算过去了”时,前面还有一句话,“还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那样伤心的人,她昨晚在大使馆痛不欲生,因为她的好儿子已阵亡,那所古老的庄园得让侄儿继承了。还有贝克斯巴勒夫人,人们说她主持义卖市场开幕时,手里还拿着那份电报:她最疼的儿子约翰牺牲了”。也就是说,伍尔夫用看起来漫不经心的语言告诉读者,战后的第一个六月天,看似一切都没变,但其实,战争与死亡为这些恍若隔世的欢声笑语奠基,正如后文主角的自杀会为小说高潮的宴会奠基一般。
欧洲的“最后一个夏天”再也不会复现。这正是整部小说最核心也最隐微的牵引之力——死者为生者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