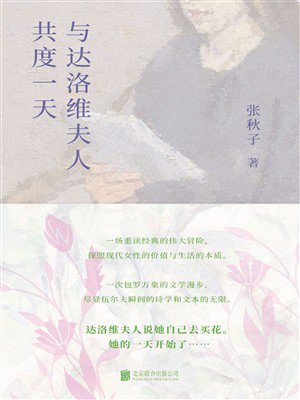2
现代性意味着流动性。
相比从前,人从固定的土地、位置、身份与职业中跳了出来,社会学家们会用“脱域”(disembedding)来形容,而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回想自己在上大学离家前夜的惶恐和期待,以及工作后四处出差旅居的疲惫和刺激,就能明白,现代人已经在更大的时空中体验不确定性与过渡性了。国内年轻人对于编制和“上岸”的执着,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他们被抛到了一片动荡之海中,人们在定所与漂泊中来回折返。
置身水中乍听起来不太妙,因为这时人的身份与故事都会变得模糊不定,可是几乎所有的文明都相信海洋与河流是文明的起源。在古典文学中,作家们不厌其烦地讲述漂流中的冒险,而现代作家对现代生活的描述也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水体景观。早年漂泊于海上的麦尔维尔坦言:“所有的人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会生出向往海洋的感情,和我相差无几。”济慈的墓志铭是:“这里长眠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T.S.艾略特干脆把《荒原》的第四章定名为《死于水》,并为读者们留下了一具随波沉浮的永恒的尸体……至于伍尔夫,当她开始描述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时,动用的依然是她最喜爱的水体景观。大海、海浪、瀑布、河流、雨水、滨河、湿地、池塘、沼泽、水池……所有这些水的形态都高频率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只不过,与《到灯塔去》《海浪》等作品不同,《达洛维夫人》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含水量很低,纯然是一个内陆城市的干燥故事,水只会以记忆中的浪涛声或在关于水体的比喻中出现,人们在讨论到伍尔夫笔下的水时,也很少会拿这一部分说事。但是,《达洛维夫人》中人的思绪飘移,又是用水的形态展开的。
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的文体即水体,读者即泅泳者。我们必须学会相信水的规律,才能漂浮前行。
在本细读章节的开始,伍尔夫描述了一声爆炸,原来是花店外面汽车的车胎爆炸了,车里坐着一位神秘的大人物,于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那里。这段描写可能来自伍尔夫自己在伦敦购物时的经历。1915年2月1日,她同样在街头听到了一声爆炸,在日记中,她试图分辨那到底是什么声音,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她的注意力一半被声音吸引,另一半则迅速观察着周围那些同样被吸引了的人。她的观察被转换到了以下的描写中:
然而顷刻之间,谣言便从邦德街中央无声无形地向两边传开,一边传到牛津街,另一边传到阿特金斯街上的香水店里,宛如一片云雾,迅速遮住青山,仿佛给它罩上一层面纱;谣言确实像突如其来的庄重和宁静的云雾,降落到人们脸上。瞬息之前,这些人的面部表情还各自不同,可是此刻,神秘的羽翼已从他们身旁擦过,他们聆听了权威的声音,宗教的圣灵已经显身。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使不可见者可见。
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都听过流言蜚语,也可能都传过闲话,但是,没人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碎语传播的方式展现出来。所有的碎语与谣言中都包裹着不确定的信息与惶惶不安的忧虑,水则是最能传递这种不安与不确定的载体。在这里,读者会发现伍尔夫选用的词语都是与水有关的,比如说谣言从街中央无声地向两边传开,“传”的原文是“cir-culation”(流动、传输、循环之意),这个词会让我们想到人体内部血液的循环流动;音波在人群中传送时,作家两次将其比喻为无形无声的云雾(cloud),云本身就是大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的小水滴或小冰晶。更有趣的是,伍尔夫哪怕在形容钟声传送时,仍然用的是和水有关的词,比如“flood”(充溢、泛滥、洪水之意)。
不仅人们说话的内容与感受被液态化了,消息传递的路径也像河流溪水一样会分叉。当达洛维夫人告诉休自己在漫游时,这场流动就开始了。但故事并未将她视为主流,她也不过是伦敦万千市民支流中的一条。大家的第一个汇流处就是那辆突然发出爆炸声的汽车,正当这声爆炸激起了人群的注意时,伍尔夫又荡开一笔,开始细写每个人不同的反应,这样,小说的焦点就从克拉丽莎自然地流淌到了同样听到响声的赛普蒂默斯身上,他是小说中的另一位主角。以爆炸声为中介,人们的思绪汇聚又分叉。这种写法其实很具有游戏性质,让我想到曾经目击的一个孩子的游戏。
我家小区的外面是烧烤街,店主的孩子每天都在街头玩。有一次,我看到其中一个小女孩拿着筷子在人行道上划拉了很久,走近了以后才发现,她在“造河”。她家铺子里的水淌到街上来,汇聚了一大摊,她拿着筷子,沿着人行道砖块的缝隙把这摊水洼分出新的“河道”,很快,路面上出现了好几条沿缝而行的细流,歪歪扭扭,分流了那一大摊水。在那一刻,我觉得小女孩在做着和伍尔夫一样的工作,就是改变水体的形态。
孩子与作家感受到的可能是一样的创造性的快乐。
人们常说“水往低处流”,水的流势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众人注意力与思绪汇聚又分叉的过程中,也有一种情感规律始终牢牢统治着他们:对大人物的崇拜。伍尔夫用一种近乎漫画的方式解释了人们动作如此统一的原因,也在其中流露出轻微的讽刺味道:人们会因为觉得大人物也许近在咫尺而备感荣耀——“这当口,他们国家永恒的象征——英国君主可能近在咫尺,几乎能通话哩。对这些普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伍尔夫在伦敦时加入了具有波希米亚性质的艺术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所以她的政治立场很自然有一些“左”倾。她对皇室与政治上的大人物一向不以为然,甚至写过一些带有温和否定气息的政论文章,只是由于编辑担心文章是在“攻击皇室”,始终没有发表出来。
在这个细读章节中,伍尔夫以水的形式写出了街头众人的景观,读者的视线一直不间断地跟随着不同角色的思绪之流漂浮,从主角流向配角,从只出场一次的人物又荡回到恒定的角色。但是,我发现伍尔夫没有精确地写人们的动作,只是模糊地告诉读者,他们在听、在聚集、在看、在停驻。比如说雷西娅挽着丈夫的手臂走,但只是以夫妻的名分这样做的,并不带感情,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个挽法;再比如萨拉抱着孩子,那孩子一直在乱踢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几个月大的孩子在怀里简直会像刚捕上来的鱼一样扑腾,非得用蛮力才抱得住,萨拉又是如何抱住孩子并抬头看天的呢?也就是说,在城市表面漫游的伦敦人的动作是模糊的,也是不连贯的,相比之下,倒映在他们心灵中的思绪则有一种持续之感。
动作模糊与行动断裂之处,思绪却绵延如河。
我在阅读小说时,一度非常喜欢对动作精细的刻画,如果一部小说中的动作能被还原出来,简直令人喜悦。比如乔伊斯在《死者》里刻画一个微醺的男人,他一边和人讲故事,开怀大笑,“同时用他的左拳的指关节来回揉着他的左眼”,这个动作意味着他想让自己清醒过来;或者耶茨《复活节游行》中形容一个人表示自己又忘了事,“用掌根部击打着自己的太阳穴”,这个动作则意味着他的恍然大悟与懊丧。在课堂上,我邀请大家设计动作来表现试图让自己醒酒和恍然大悟的懊丧这些情绪,一个好玩的现象出现了,没有经过写作训练的人在表达情绪时往往比较抽象和粗略。
比如有同学说她怎么表达突然想起某事的懊丧呢,她说:“用手拍脑袋”,可这是一个很模糊的动作,因为看到这句话,你既可以认为是用手掌拍脑瓜顶,也可以认为是握拳捶打脑门。可是,作家的写作中有一种“一击必中”“舍此无他”的精准,所有人读到乔伊斯的这个描写时都只会做出同一个动作——一时间,课堂上的同学们都开始用手掌根部击打自己的太阳穴。
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会刻意描述精确的动作,用以传达一个人最内在的性情。大家常常说一个词叫“躺平”,就是不想去“卷”了,有点放任自流的意思,当我躺在床上玩手机时,发现真的需要努力才能再起身下床做事。就说“躺”这个动作,在小说中就赢得了大量有目的的呈现。比如海明威在《杀手》中描述了一个高个子的拳击手,当他得知有两位杀手要来杀自己时,他的动作始终是躺着,床根本容不下他的身量,而且海明威几次写到他面朝墙躺着。不合身的床、始终躺着的姿态、面朝墙的方向,这一切都透露出这个拳击手的被动性,他面对自己的丧命是毫无办法的,他犹如困兽般无奈地等待着命运的降临。类似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写了一个贵族的躺,当他得知自己的新婚妻子的风流韵事时,他却只能躺在沙发上看书,“好像一只被猎犬包围的兔子,竖起耳朵,在敌人面前躺着不动”。这个动作透露出他在婚姻中弱势的地位,面对婚外情却无能为力的孱弱姿态,这场婚姻本来就结得稀里糊涂的,而这个女人他从来不能驾驭。
这些动作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我想作家最伟大的地方更在于表现无意识的动作,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做出却被忽略的动作。还是在这堂课上,我邀请一个男生设计动作时,他说自己实在是想不出来,这时候他用手抓了抓脑袋左边的头发,我提示他说你做了一个无意识的动作后,他很不好意思地又用手抓了抓右边的头发,这仍然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我们每天要做多少无意识的动作啊,可是哪怕有一个会被记取下来吗?塞林格的《与爱斯基摩人打仗前》中也写过一个男生的无意识举动,他在说着话,忽然间“用大拇指刮蹭自己的脊梁骨”。我想不起自己做过这个举动,但是一定见别人做过类似的动作。我甚至有些夸张地认为,仅仅是对于这个无意识的动作的捕捉就足以让塞林格进入一流短篇小说家的行列。他有超乎普通人的敏锐,鹰眼一般打捞和筛选日常生活激流之下的小小鱼苗。
可是,在《达洛维夫人》的这个细读章节中,最为具体的一个动作也无非是说惠特酒店里的男人看到神秘的黑车驶过窗口时,纷纷站在酒店的凸肚窗前,“手叉在背后”。要不是伍尔夫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被不朽的伟人放出的淡淡的光芒攫住了心灵,读者还真不知道把手背在背后观望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毕竟,一个中国的老大爷也会在早晨遛弯时把手叉在背后,逗弄笼子里的画眉。在更多的时候,伍尔夫笔下的人物动作和姿态就像是被滴了一滴水后洇开的模糊轮廓,读者无法从中窥见一个人的性情。也就是说,她基本放弃了对外部动作的精细刻画。
她同时放弃的还有动作与行为的连续性,一个角色可以出现一次就消失,泥牛入海一般。我们的同学在初读这些段落的时候很不适应,大家总觉得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登场了,是不是就会和咱们的主角发生点什么故事呢?可是,在本章节中,抱着孩子的萨拉、矮小的鲍利先生与他的科茨太太,全都只出场了一次,说了点什么,或者想了点什么,然后就消失了。而且,大家也习惯了主角登场后,故事就应该围着他转,怎么才讲了两句,又去讲别的人了?很多人读到后面,才发现本书是双主角模式,赛普蒂默斯也是主角之一。整个小说基本是在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的所闻所感之间穿插切换。
这还挺让人纳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