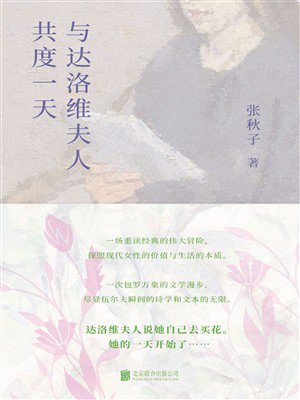3
行动的连贯曾是小说的核心。
从《圣经》开始,故事就通过对行为和行动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思想,于是,作家们费尽心思设计行动,推进行动,还得考虑怎么把这个行动和那个行动连起来,让一个角色得到充分的理解。所以,传统的小说非常注意“情节冲突”或者“巧合”,为的是将所有的行动合理且戏剧性地串起来。
翻开《安娜·卡列尼娜》,找到一个关于露齿大笑的动作,读者就能明白什么是古典小说里强调的行动的连续性。整部小说的核心事件是女主角安娜受到了一位风流浪子沃伦斯基的引诱,两人私奔,但最后沃伦斯基还是厌弃了安娜,安娜终于卧轨自杀。在风流浪子刚刚登场时,托翁反复写他有一排“整齐的牙齿”,从里面会传出“健康的笑声”。咬合良好又洁白的牙齿让人想到咬碎一个东西时的力量和笃定,试着回想一下我们用后槽牙压碎一颗坚果,榨出里面芬芳的油脂的情形,咬碎的动作诉说着我们的健康。我想托翁意在用这排美牙传递出它的主人赢得美人芳心的志在必得,就像猎豹咬定自己的猎物不放松一样。
 当托翁笔下的这位牙齿美白的风流浪子厌倦了安娜后,他那阔大的牙齿突然开始剧痛,嘴里充满了口水,似乎无意再捕获什么女人,牙齿的病变乃是情感的病变。如果把小说前后关于牙齿、微笑、咬合这些细节串联起来,读者会看到一幅完整连续的行动变化图:一开始对女人的追求与露齿大笑,以及厌倦后剧痛的口腔与坏牙。小说中似乎处处布满了呼应的巧合与冲突。
当托翁笔下的这位牙齿美白的风流浪子厌倦了安娜后,他那阔大的牙齿突然开始剧痛,嘴里充满了口水,似乎无意再捕获什么女人,牙齿的病变乃是情感的病变。如果把小说前后关于牙齿、微笑、咬合这些细节串联起来,读者会看到一幅完整连续的行动变化图:一开始对女人的追求与露齿大笑,以及厌倦后剧痛的口腔与坏牙。小说中似乎处处布满了呼应的巧合与冲突。
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达洛维夫人》的这个细读章节,读者大概会铩羽而归。伍尔夫笔下是以碎片化的方式来交代人物行动的,当飞机出现在天空时,每个人的行动都只被捕获了一个瞬间:
“Blaxo,”科茨太太凝视天空,带着紧张而敬畏的口吻说。她那白嫩的婴孩,静静地躺在她的怀中,也睁开眼望着天空。
“Kreemo,”布莱切利太太如梦游者一般轻轻低语。鲍利先生安详地举着帽子,抬头望天。整个墨尔街上的人群一齐站着注视天上。
…………
在摄政公园的大道上,卢克丽西娅·沃伦·史密斯坐在丈夫身边的座位上,抬头观看。
读者无法再进行勾连和推断了,因为行动的连续性被偶然性取代了。这一幕真实地还原了一个人走在路上时看到的景观:只可能注意到路人的一两个动作,而且无法从这些零碎的动作中推断出关于这个人更多的信息。其实,连贯的动作会更依赖有逻辑的想象,而偶然的动作则更依赖对生活的警觉。
在这个细读章节中,不仅动作是模糊的,行动也是偶然与断裂的。不过,偶然性的行动并不是伍尔夫的发明,用偶然与无稽超越刻意的冲突关系,在十九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就有所显露。
我还是用上文提到的《安娜·卡列尼娜》为例。这本书确实充满了连贯的动作,但它还有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细节,它破坏了全书的连贯感。主角的哥哥爱上了一个姑娘,他决定在树林中采蘑菇时向她表白,内心也演练了好几遍表白的话,终于,围在他们旁边的孩子已经走开,姑娘也猜到了男子的心意,兴奋和恐惧得心都缩紧了。可是,姑娘突然违反心意,脱口而出:
“那您真的什么也没有找到吗?其实树林里总要少一些。”
他的回答则是:
“我只听说白蘑菇多年都生在树林边上,可是我也不会鉴别哪些是白蘑菇。”
(草婴译)
告白就这样结束了,什么都没发生,就像气球被放了气,除了关于蘑菇的一些知识,我们也什么都不知道。故事里似乎少了一环,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导致两个人都没有把爱慕之情说出来,可是,托翁始终没把断裂的动作补上,当然也没有把两个人内心的想法交代出来,告白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败了,甚至,两个人的这场采蘑菇的戏也显得偶然和无稽。
实际上,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小说中,“突然”“无稽”这些断裂的行动构成了某种核心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人物会突然做一件事,这件事往往无法和此人之前的行动搭上关系,也没法解释他之后的行为。《群魔》中的主要角色斯塔夫罗金一开始显得特别正常,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学识颇为渊博,一向彬彬有礼地出入于上流社会。但是,有一次在和某位俱乐部主任谈话的过程中,斯塔夫罗金突然伸出两只手捏住主任的鼻子,抓着他在大厅里走了几步,读者的唯一线索大概就是主任吹嘘过自己:谁也别想牵着我的鼻子走;而另一次,当亲戚问他为什么突然行事如此乖张之时,他假意凑过去要告诉人家原因,却一口咬住了亲戚的耳朵……对于这些莫名其妙、突然出现的行为,似乎连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无法解释,他只能一摊手,耸耸肩说:“只有鬼知道这是为什么……”
近代也有一些作家喜欢突出这种连续动作之中的无稽性与不可解性。比如,奥康纳在短篇小说《帕克的背》里描述帕克是怎么与妻子结识并结婚的,每一次帕克都觉得这个女人实在是又不好看又无趣,但下一次他仍然莫名其妙地来到了女人身边。写两人结婚的细节简直堪称“神转折”:当帕克想要和女人在车后座发生关系时,女人严词拒绝了婚前性行为,因为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甚至把帕克推倒了。帕克“下定决心,不要再和她纠缠下去了”。读者这个时候大概也会附和帕克,觉得这两人真是够了,既然始终无法磨合,干脆一拍两散、一别两宽。但是,令人大呼意外的是,奥康纳换了一行,在下一段里马上写道:
他们是在本地教区长办公室里成婚的。
(于是译)
奥康纳把人物行动中的无稽与偶然表现得更为“锐化”,当一个大转折蓦然发生时,其令人费解的尖锐简直能够刺伤人。我在课堂上复述这部小说时,很多同学都错愕地惊呼了出来,因为一个人行动里的偶然性切断了读者想象的一切连贯的可能。它不是单纯为了刺激读者的所谓“反转”——那种悬疑剧中最常见的平庸手段——而是激发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人的行为真的能让我们窥见人的本心吗?
无论是俄罗斯作家群还是奥康纳,他们似乎都窥见了一个人行动里混沌与荒诞的地方,向更深处的窥视实际上都暗示着作家们将对人的推敲转移到了动作之下,从可见的行为本身转移到了支配行为的心灵之上。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
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再读到小说中人物让你费解的行为时,也许可以不必再费心地去弄明白原因,倒不如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近现代小说倾向于呈现人身上难以解释的地方,毕竟,我们看到身边很多人的行为时,也常常觉得匪夷所思、难以诉诸理性呢。有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和我聊到自己是如何渐生防备心的。她毕业后到书店工作,每天都看到一位老爷爷来店里看书,可能因为觉得自己没付钱却一直看书,他还不好意思坐在店里,一直坐在店门口的花坛边。女孩很感动,她对读书人有天然滤镜,又觉得老人很慈祥,还去给他送过茶。但是在一次值夜班的时候,这位老人喝醉了,拎着酒瓶闯入书店,对女孩做了一番颇为猥亵下流的评论,当时女孩吓坏了,觉得这个行为与他之前的行为根本连不上,仿佛他突然暴露出自己的本性来。喝酒不是原因,更像是掩饰。这就是人行为中不可预期的断裂。
当然,我还得强调一下,上述这些作家在模糊了行动的连贯性后,仍然把解释这些行动的思绪藏了起来,直到伍尔夫,才打断了行动的脊梁骨,围住了思绪,从而让行动的连贯变成了思考的流动。这是现代意识流小说对传统作品最大的颠覆与改变。
我也意识到,现代意识流小说中,思与行的断裂是永恒的,大段绵延的思绪必然以行动的中断为代价。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其实很难产生长时间的浮想联翩,因为他会被白天外界的各种琐事打断,或者被晚间的睡眠吞没,哪怕是彻夜失眠的人,也会有翻来覆去的动作,像《尤利西斯》最后一章莫莉长达几十页的幻想,根本只能是纯文学的产物。我当然明白,作家们这么“悬浮”地描绘意识是有其美学追求的,当读者艰难地阅读着福克纳笔下自杀者长达数页的心理活动时,那些铺张蜿蜒的句子简直就像一支看不到头的送葬队伍,将主角护送到冰凉的河底。只是有时候,我因为太过好奇,倒还是很想邀请同学们为大段大段幻想着的人增补几个动作,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光想就想了十几页。
其实,伍尔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她非常妥善地处理了小说中人物思绪的节奏性,在她的笔下,很少会看到福克纳或者乔伊斯笔下连着幻想和思考几十页的悬浮之人。她的妙,在于她会捕捉刹那之思。
刹那之思与漫漫缅想构成了小说水面之下两股速度与压强不同的水流,彼此交错。
在本细读章节里出现了飞机,它所刺激的思绪就是刹那之思。人们抬头仰望天空,看到飞机拖出长长的尾巴,继而根据自己的想法拼出文字,也就是说,伍尔夫此时以一种即兴的瞬间思绪拼凑出众人的思绪之流:有的人想到的是Blaxo(一种香皂),有的人想到的是Kreemo(一种乳制品品牌),有的人则是toffee(太妃糖),每个人的思绪都由她的经验决定。这也再一次呼应了前文中达洛维夫人看到铺子里的鲑鱼、珠宝和花呢时说:“这就是一切。”——它指的是,你是什么人,就只能看到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又反过来强化你所是的状态,人与物因此处于一种互相解释的循环关系之中。对于一个孕妇来说,她会觉得街头的孕妇比平时多得多;对于一个名牌爱好者来说,他对人的观察也往往只筛出了各种logo(标志);对于伦敦街头的这些主妇来说,她们的生活是围着清洁工作与饲育工作展开的,所以,她们也只能联想到糖果、乳品和香皂。由此,伍尔夫为我们传递出一个人类生活的侧写: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超过他日常经验的水位线,人们困在自己的昼夜与琐事中。
对刹那思绪的捕捉,也许还暗藏着伍尔夫的教导:在个人伦理生活的核心,仍然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它需要得到尊重——内心的秘密是不可侵犯的,不要试图通过长篇大论的意识流描写把一个人吃干抹净、搜刮一空。
似乎,与男性作家的意识流写作相比,作为女性的伍尔夫是有余让的,也是克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