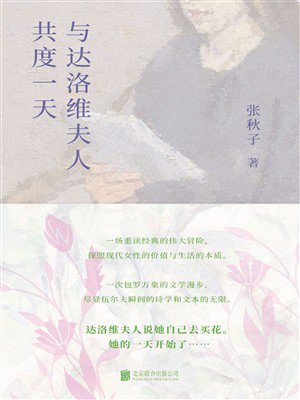4
在1929年的一篇小说《游泳池的魅力》里,伍尔夫区分了水面之上与水面之下的景观。
讲故事的人坐在池边,看到了旁边的白色广告招牌以及上面红红黑黑的文字,但她更感兴趣的是倒映在池面的影子。微风吹过,水面的倒影就像一件被涤荡的衣服,当人们凝神,会发现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奇特魅力,表面上似乎很薄,但水下面却在进行着某种深奥的生活,仿佛是心灵的沉思默想。显然,伍尔夫非常关切表面和内在的两种生活状态。在《达洛维夫人》中,表面的生活是人们在城市中的漫游,而倒映水下的,则是他们的思绪。在创作这本小说时,她最常翻阅的书就是《奥德赛》,自然而然,充满咸味的海水从古典的希腊世界倒灌进了现代的伦敦,她的目光,则紧紧跟随“下面的”、平日里看不到的暗流。遐想之所以能展开,依循的是倒影和深度的辩证关系。
这篇小说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伍尔夫专注于意识而非动作的连续性的原因:她觉得一个人的意识会比一个人的动作更真实。其实,大家常说的成语里也表达过类似的智慧,比如“人面兽心”“装模作样”“色厉内荏”“笑里藏刀”“人模狗样”……这些成语都在强调人外在呈现的不可靠,只是没有用一种小说化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中对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真实性的颠倒差不多到了十九世纪末才大规模地发生,而且这场变化深刻地混入了整个近代社会认识论的变化潮流中:为什么个人主义会在近代崛起、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会在十九世纪以后大行其道、为什么印象主义绘画很快盖过了古典主义的风头……所有的这些现象可以说都意味着一件事:人们不再满足于对世界进行物质的理解了。
在这个细读章节中,众人的内在世界的状态以万花筒的形态传递出来,伍尔夫不甘于写一个人的心灵波动,她要写万千人的心灵,她要对人类的心灵史做一个掠影。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具体的意象,想象人们是如何被巨响刺激并组织起来的:一颗石子投入水中,荡漾出一圈圈涟漪,每个人都像水面上浮着的昆虫或者树叶,被编织到涟漪的同心圆中,昆虫或者树叶又因为自身的存在,激荡出更多的涟漪,彼此交织。
具有浮力的水体般的文体是对传统小说极大的颠覆,因为传统小说看上去像是一块陆地,有时候因为干燥缺水,会出现板结和龟裂的现象。
以意大利十八世纪的作家曼佐尼的《约婚夫妇》为例,这是一部非常厚重的作品,但情节无非是有情人经过重重磨难终成眷属,并没有什么新意。读的时候,读者们会发现故事是一块一块讲出来的,比如一对年轻男女想要请神父证婚却遭遇了恶人的阻挠,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位修士做帮手,曼佐尼把这对男女一丢,开始讲起修士的生平过往;回到男孩女孩的主线后,困难仍未解决,为了躲避恶人,两人分开,曼佐尼又把男孩一丢,讲起女孩避难的修道院里修女的堕落故事;当我们都快忘了男孩时,曼佐尼终于在米兰把他找到,可一旦找到他,女孩却失踪了。
曼佐尼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既不能让两人重聚,又无法完美地交织讲述两个人的故事,于是,故事变成了板结的状态,他自己承认有这个问题,当要调转回马枪时,只能承认:
我们认为这件事还可以作为另一部作品的素材。但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需要相当的篇幅。再说,在那些事情上花费许多笔墨会干扰读者对我们的故事的兴趣。因此,我们不如在另一篇文章里记叙并探讨那些事,先回到我们的主人公身边,免得冷落了他们。
(王永年译)
读者心里不免犯嘀咕:您还记得自己在写小说哪。小时候,我守着收音机听评书,说书人还会取个巧,“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且往往在这头故事最险要的关头突然打个岔,又开始讲那头的故事,两边的故事在悬念的跷跷板上忽上忽下,把人急坏了。与此相反,我发现曼佐尼根本不在乎什么悬疑的设置,他会一直讲一块故事,直到我们已经不关心其他人物的存在,直到这一块故事没什么可讲的了,他才重新捡起另一块。远远望去,整个小说就是各种无关的故事模块拼在一起,边缘缝隙极大,几乎没有有机关联。
这当然不是曼佐尼自己的问题,况且《约婚夫妇》在其他方面仍有可称道之处。由于整个传统文学世界都极度依赖情节,情节模块的组织又往往非常程式化,很多小说都是作家在民间传说口口相传的基础上整理起来的故事集,板结和龟裂的情形就时有发生。《一千零一夜》《十日谈》《堂吉诃德》都是块状叙事,也就是把一堆故事凑在一起。只不过,有的作家会在不同的故事模块之间多上一些“润滑油”有的则听之任之地让其干燥结块下去。这其实是我们分辨好作家与坏作家的一个准绳。
由于对故事情节的淡化、对动作的模糊以及对思绪的持续追踪,《达洛维夫人》的整个故事是流动而非板结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小说失去了确定感与立足之境。对现代作家来说,小说的思绪太过流畅也是个问题。伍尔夫和朋友聊过对写得“单纯的流畅”的担忧,在1924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她做了一个关于水的比喻,说重新把这部作品打理了一遍,“就像理发,用湿梳子将它整个地梳理一遍,把分散写出的部分一起理顺畅”。所以,她需要一些更坚硬的东西,像楔子或者钉耙一样插入文本,固定思绪,一如海上灯塔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流动性与固定性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
我请同学们试着抓取这段细读文本中的坚固之物。他们抓到了建筑(维多利亚大街、布鲁克街、白金汉宫、圣·詹姆斯街、皮卡迪利大街、摄政大街),雕像(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后文中戈登的雕像、战士的黑色雕像),还有,大本钟。这些城市的象征符号与公共建筑体现出城市“超凡”的一面,所以能够牢牢抓住行人的注意力。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公共建筑的超凡入圣又会被混乱无序的扩张改建拉回地面:复杂弯曲的小路,鳞次栉比的新建筑以及吵吵闹闹的新型交通工具,一股脑全涌现出来。所以,其实汽车和飞机也算是新出现的坚固之物。聆听报时,目击飞机,围观车辆,路遇雕像,这些东西为万千心灵营造了一个“同时的感觉”。
这其实也是一种现代体验。
我的共时性体验出现得很早。小时候,生活在厂矿,每天早上七点半,厂里的广播站就开始报时,催促工人前往工厂,主持人会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告诉大家“早上八点的太阳红丹丹(红彤彤)”,所有人都处在一致且统一的时间与空间中。长大后和来自农村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的童年几乎是在一个无时间概念的环境里长大的,去水库游泳捞鱼,随随便便就天黑了。后来看社会学的书,才知道这叫作“想象的共同体”,传媒报纸、北京时间,让分散在各地的人有了一种我们“共在一个国度”的认知。
当然,也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伦敦街头吸引大家的是汽车和飞机。现代社会里,除了孩子会兴奋地指认天空的飞机,所有人都会对这些工具漠然,但对于二十世纪初的人来说,这两样东西代表新生的文明,是科学与生产力的体现。在小说中,运输工具往往暗示出社会背景的历史进程。在奥斯丁笔下,当马匹匮乏时,小姐们只能踩着烂泥步行,衬裙溅满了泥点子;十九世纪初的交通革命带来了更多碎石路、马道、大马路和公共马车,也把包法利夫人从乡下送进了富庶的小镇;萨克雷笔下的年轻人则会骑着老马去看火车驶过的场景,因为那代表着通向未来的方向与速度,令人兴奋;铁轨的铺设冲击着古老的世界,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哈代日记中的一则记录,说伦敦当时的铁路公司穿城而铺,途经一处教堂墓地,尸骨都被挖出来让路;很快,汽车的出现再一次更新了人们的兴奋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公子哥开着劳斯莱斯把人撞死。
伍尔夫对待这些现代机器是什么态度呢?
她故意让我们看不到是谁在使用这些机器:车里的手很快拉上了帘子,飞行员对地上众人来说是看不到的;甚至当克拉丽莎回家时,也只是“听到”打字机的哒哒声,浑然不知是谁在打字。这种不可见最后是否指向了那些统治着我们的权力的不可见,甚至发动和指挥战争之人的不可见呢?与兵戎相见、面对面的传统战争相比,现代战争依靠的东西变成了一粒按钮、一块屏幕、一道射线,没有人知道按下发射原子弹按钮的那只手来自谁,也不知道喷出毒气的阀门又是由谁转动。参战者赛普蒂默斯成了不可见的牺牲者,读者会注意到,当街头所有人都被汽车和飞机所吸引时,他却漠然无感。
我想伍尔夫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了,她与卡夫卡达成了共识:对现代技术保持警惕,对现代技术背后的暴力保持警惕。
总之,各种各样的坚固之物如同一个个楔子,或者钉子,插入文本,防止人们的思绪游离无边,营造出完美的共时性的感觉。不过,这些楔子却并不完全一样,至少,聆听报时的钟声与目睹飞机汽车或者雕塑建筑有很大不同。听觉相对视觉来说更为被动,你可以通过调整视角来变化远景和近景,可以安排和整理进入眼睛的世界,但却无法拒绝与改变涌入耳蜗的钟声。这近乎一个隐喻:人们无法抗拒时间的流逝,而时间的流逝巩固了某种最坚固的无形之物——社会的制度,它不仅将所有人收拢进一个共同体认知里,而且还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所以,伍尔夫写下了这段关于婚姻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话,这也是在课堂上大家表达过最多困惑的一段话:
多少年后,伦敦将变成野草蔓生的荒野,在这星期三早晨匆匆经过此地的人们也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唯有几只结婚戒指混杂在尸体的灰烬之中,此外便是无数腐败了的牙齿上的金粉填料。到那时,好奇的考古学家将追溯昔日的遗迹,会考证出汽车里那个人究竟是谁。
伍尔夫没读过什么社会学家的高论,但她深深感到,这个社会最不可撼动的,恰恰是已成惯例的习俗,人们对待性别、婚姻、生育、战争、阶层等制度的态度,莫不如此。当巴黎圣母院被付之一炬,当巴黎狭窄的小路被拱廊街所取代,当伦敦的水晶宫被毁于一旦,习俗还在,你还得结婚!还得生娃!那枚在枯骨中依然坚固的结婚戒指,透露出深深的哀叹与讽刺。与其说伍尔夫是在描述种种制度的持久,不如说在讽刺它们的顽固,活着的人被“该怎么做”的方法论牢牢统治,浑然忘了是死去的人定下这些规则。时间的海啸只是一次次强化着制度的堤坝,而并没有损害其分毫。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读书时不允许早恋的告诫与工作后被催婚催育的观念无缝切换、并行不悖,“必须结婚生子才是完整的人生”的想法也深深印刻心中,比任何有形的东西都坚固。
但是,人与动物的不同又在于,人不会永久地栖息在历史与习俗的余荫下毫不动弹。
由是,伍尔夫在日记中发出强烈的渴望:“我想描绘生与死,理性与疯癫;我想批判社会制度,展示它是如何工作的,在它最激烈的状态下。”
《达洛维夫人》在很多微小的地方对这些最强悍的固定存在物发起了攻击,我们稍后就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