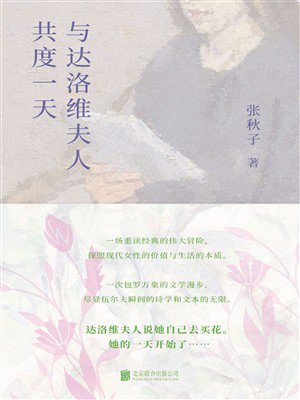1
文学有时需要经过生命经验的处理,才能真正被理解。
在细读《喧哗与骚动》时,作家提到,儿子在父亲的墓地边“突然觉得好玩,便决心在附近逛一会儿”。我的学生表示不能理解这种心情,哪怕父子感情再不好,在那个严肃的时刻,也应该全神贯注于生死大事,除非作者就是要写儿子的全无心肝。直到她后来跟我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她与室友养了好几年的猫突然得了猫瘟,被抱到宠物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两个姑娘在医院里哭到没有力气,只有把猫抱回。整夜,猫都一直在哀号,可能是因为“眼泪都哭干了”,姑娘们无法彻底沉浸在悲伤里,时不时竟还聊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愉快的事情。有时候,因为猫的叫声太烦人,她们还会抱怨两句,觉得睡眠被严重地影响了,聊天闲扯和抱怨就像忍不住开的小差,溜进了这个死亡之夜。第二天,猫终于身子一挺,排出一些粪便后便死了,粪便温热,身体僵硬,粉红色肉垫全都变成了黄色。
在她不可自抑的分心时刻,她突然理解了那个儿子的态度:没有人能持续不变地沉浸在一种高强度的痛苦之中。文学说的是真的。山多尔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也问我们:你了解这样一种感受吗?当一个人在生活最悲剧的阶段,超越了痛苦和绝望,一下子变得特别无谓甚至心情愉悦?
比如,当人们要埋葬一个最亲近的人时,突然想起忘记关上冰箱门,狗因此可能会吃掉为葬礼酒宴准备的冷肉……在下葬时,当人们围着棺椁歌唱,你已经开始下着指示,悄声而平静地处理冰箱这件事……因为在本质上,我们生活在这样没有尽头的彼岸和永无止境的距离之间。
(郭晓晶译)
在这样一个应该屏息凝神的时刻,人们就是会分心。哪怕是在不那么悲剧性的场合,仅仅是需要严肃、认真和专心的时候,人也总忍不住开点小差。我的职业一度使我必须和走神作斗争,“手机放下头抬起来”成了我在上课前负隅顽抗的冲锋号,毕竟,不间断的短视频和消息推送早就在和我争夺注意力的阵地。刚登上讲台时,我甚至想出了好多办法来对抗分心,比如学“新东方”写逐字稿,讲到第十分钟的时候来一个段子,讲到半小时的时候组织一次讨论,卡点放送,还算屡试不爽……但是,随着阅读与对人的理解的加深,这些年反而松弛了很多,有时候瞥到台下一张显然已经走神的面孔时,我更想共情于她的“索然”——她也在想着什么关于“盘中冷肉”的事情吗?
我甚至有点想要赞美走神了。因为,我在这么思考着她的时候,也在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