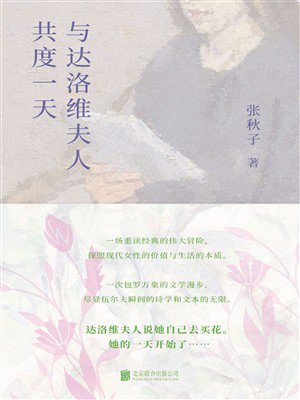3
文学中的分心让一些人逃逸与减负,相反,专注可能让人沉重,尤其在我们过于关注自己的痛苦时。
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疼痛感会争夺你的注意力。感染新冠肺炎的时候,我除了发烧还有一个症状是下腹疼,不算剧痛,是拉丝般的痛。我总觉得还算能忍受,于是仍然打算坐在桌边开始工作,可是,一丝丝的疼痛无时无刻不在剥夺我的注意力,我的专注力全部转移到了感受这种疼痛上来,我最终放弃抵抗,回床上躺平。昆德拉在《不朽》中也写了一个女人的脚走得很痛,而且,她也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痛苦的感受上:
又走了很久,双脚疼痛,踉踉跄跄,然后坐在公路右边中央的柏油路面上。她的头缩进肩膀,鼻子顶在膝盖上,弓起了背,想到要将背部去迎接金属、钢板、撞击时,她感到背部在燃烧。她蜷缩成一团,将她的可怜而瘦削的胸部更加弯成弓形,疼痛的自我妨碍她去想别的东西,除了她自己,这自我的烈火在她的胸膛中升起。
(王振孙、郑克鲁译)
昆德拉非常警惕人陷于自我之中。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自我感动都是避之不及的恶疾。通过描述一个女人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脚痛之上,昆德拉向那些陷入自己的小世界中不能自拔的人发出了轻轻的笑声。注意力的集中,可能会导向另一个局面:过度的自我沉溺——不加控制地放纵自己的感受,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的感受,再不顾左右地大量谈论这些感受,旁人的反应,大概只剩下不胜其扰了。
在这个细读章节中,伍尔夫则用充满怜悯的笔触描述了雷西娅的孤独绝望,这是由于一门心思扎到自己的处境里引发的:她的丈夫本就不爱她,在经历了战争创伤后更是沉迷于幻觉。当发现无法把分心的丈夫拉回现实世界后,她无奈地感叹:“爱,使人孤独。”小说提供了这样一段描述:
孤零零地站在摄政公园喷水池边,她呻吟着(一面看着那印度人和他的十字架),也许好似在夜半时分,黑暗笼罩大地,一切界线都不复存在,整个国土恢复到洪荒时期的形态,宛如古罗马人登陆时见到的那样,宇宙一片混沌,山川无名,河水自流,不知流向何方——这便是她内心的黑暗。忽然,仿佛从何处抛来一块礁石,她站在上面,诉说自己是他的妻子,好几年前他们在米兰结婚,她是他的妻子,永远、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他疯了!她转过身子,礁石倾倒了,她渐渐往下掉。因为他走了,她想——像他扬言过的那样,去自杀了——去扑在大车底下!
怎么来描写人的孤独与无人可诉呢?
在这里,伍尔夫动用了许多过于庞大的词汇:罗马人登陆、所有国境线消失、山川河水;在中译本中,为了增加朗朗上口的感觉,还多译出了“宇宙一片混沌”这种原文阙如的说法。另外,“礁石”一词也不准确,原文为“shelf”,也就是陆地延伸到海水中的一部分,被称为陆架。也许,伍尔夫不是要呈现一个女人站在一块礁石上,突然脚下踩空跌入水里的感觉,她要呈现的是一种渐进的窒息感,是水平面上升,陆架随之被慢慢淹没,最后人沉入水中的淹没之感。水是从下往上把人淹没以至淹死的,这不是一个瞬间的动作,也就意味着,雷西娅的痛苦感持续很久了。
在这处引文中,还有一个被灌注了最多注意力的词。我们可以数一数,哪一个人称代词出现得最多?——“她”。孤零零的她。在进行文本细读时,最为简单的人称代词里往往也会包藏着小小的秘密。如果一个作家显得不顾文法、不顾文本的协调,大量使用某个人称代词,他也许正是想把这个代词之下的人推到台前,让角色赤裸裸、孤零零、支棱棱地站在读者面前。伍尔夫明明可以显得更简洁,可是她仍要执拗地把每一个“她”饶舌般摆出来,正是因为她也要突出这个角色的被凸显和放大出来的孤独,唯有刻意和突兀地使用人称代词才能实现效果。我在后文还会继续讨论细读中的人称代词用法。
看得出来,伍尔夫仍旧和很多传统作家一样,执着于辞藻的华丽。在日记中,她记录了朋友对这部书的评论:“装饰极其美”“偶尔美极了”。这种执着在当代作品里变得非常罕见。同样是写亲密关系里的孤独,当代作家可能会选择更冷峻、更简洁也更日常的方式。
比如,拿一条被子说事。
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失眠的夜里,听着室友们磨牙、梦话和轻轻打呼噜的时候,心里会有点嫉妒,怎么他们就睡得那么香?我怎么就死活睡不着?也会涌起一阵孤独,只剩自己被撇下了。醒与睡之间的隔阂远比醒着的人之间更深,你永远无法期待睡着的人张嘴说话哪怕他在装睡。没有希望开口的、被撇下了的、被落下的感觉,在卡佛的《学生的妻子》中被捕捉到了。卡佛也想呈现夫妇之间缺乏交流的淡漠,男人醒着的时候就大谈诗人作家、学术思想,浑然不顾妻子的兴趣,要么,就是妻子回忆起过往时,男人一概回答记不清了。当男人睡着后,女人依然醒着,她看到丈夫的样子:
他在床中央躺着,被子缠在肩膀处,头的一半压在枕头下面。
(小二译)
这是个非常打动我的瞬间,甚至,我觉得卡佛比伍尔夫在这点上写得更好。
描述两个人的情感淡漠和自我的孤独,不需要动用天大地大的词,只用轻轻说件日常之事: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先睡着了。听着别人已经酣睡的声音,会加剧人的焦虑感与孤独感,因为清醒者就是被抛弃者。现代人说起“孤独”好像不是个多么令人难受的状态,因为流行观念会告诉你“享受孤独”,社交平台上“独处”“独行”“独居”甚至“离婚”都会成为带来流量的tag(标签),但是,这可能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对“孤独”改造后的结果。至少在西方的十七世纪,没有人觉得一个人出去散步或者度假有多幸福,画家也不愿把自己画成铺天盖地的荒凉景象中一个渺小的角色。如果我们在莎士比亚的字典里查阅“孤独”(alone)一词,会发现它与焦虑和恐惧的关系比享受更密切。哈姆雷特王子当然有“我想静静”的时候——“现在我独自一人”,可是,那还是为了想清楚乱局,为了解脱。
在课堂上,讲到这一章时,有同学说,两个人之间最大的隔阂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人。我以为这是他从书上看来的话,但是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他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我觉得这句话真妙啊,也许足够概括雷西娅的痛苦,她的注意力被与丈夫痛苦的婚姻关系全部吸引过去,无法像丈夫一样通过分心和走神获得逃脱。她越集中,就越会缩小成一个点,一个渴望两个人成为一个人而不得的点。
虽然伍尔夫在描述雷西娅的孤独时,动用了一些过于宏大的修辞,但并不意味着她不善于使用日常之物。在本细读章节中,克拉丽莎其实也有一段专注时刻。在她胡思乱想的分心中,她集中思考了自己的衰老与死亡,而这些思考正是凝结在日常之物上,比如她上楼后接触的“床”“水龙头”和“蜡烛”。克拉丽莎对自己衰老的感受变得更加清晰,因为没有邀请她赴宴的布鲁顿夫人引起了她的衰老之思。比如对比从前玫瑰一般的柔美丰盈,现在的自己“萎缩了,衰老了,胸脯都瘪了”(shrivelled,aged,breastless)
 。于是,她走上楼,走进浴室,听到水龙头在滴水:“生命的核心一片空虚,宛如空荡荡的小阁楼。”继而,她独自睡在房间中,床很窄。在这些时刻,分心的克拉丽莎开始专注于衰老与死亡,这些专注同样带来了不太愉悦的情绪。
。于是,她走上楼,走进浴室,听到水龙头在滴水:“生命的核心一片空虚,宛如空荡荡的小阁楼。”继而,她独自睡在房间中,床很窄。在这些时刻,分心的克拉丽莎开始专注于衰老与死亡,这些专注同样带来了不太愉悦的情绪。
从克拉丽莎回到家后,一直到她上床,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空间变换路线。先是街上,然后来到家宅大厅里,“大厅凉快得像个地窖”,继而上楼,在窗前停留片刻,走进浴室,最后睡在斗室(attic,根据原文直译为阁楼)的床上。这个空间变换有什么规律和意义呢?它和每一个人的行动路线是一样的,大家也知道,人可以在户外边走路边聊天边玩手机,同时再分心看看擦身而过的美女或帅哥,但是专注则最好需要室内的安静私人空间;克拉丽莎的空间变换规律是从户外到户内,从公共到私人,这是一个暗示:人物要开始摆脱胡思乱想的分心,进入凝神的沉思了。这是一个逐渐聚焦的过程。
很多文学作品中都会出现类似的写法。比如《包法利夫人》中,夏尔第一次见到艾玛时,是按从田庄走进大宅、从大宅走近厨房、从厨房走进闺房的步骤,这似乎在呈现一个男人逐渐进入一个女人私密世界的过程;又如奥兹在《等待》中写村长丈夫发现妻子出走后开始寻找她,这时他才一点点深入与了解妻子的生活,从居所到学校,甚至他进了女厕所。这个细节非常厉害,厕所意味着女性最不洁的私密空间(大小便、月经甚至生孩子都可以在此完成),也意味着丈夫所能追回的对妻子理解的最深处。但奥兹只用了一笔来写。
进入阁楼后,克拉丽莎从分心进入对自己生命的专心思考。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那张铺着白床单的床。原文是这么写的:
宽大的白床单十分洁净,两边拉得笔挺。她的床会越来越窄。半支蜡烛已燃尽。
…………
理查德回来得晚,所以他坚持,必须让她在病后独自安睡。然而,实际上她宁愿读有关从莫斯科撤退的记载。这一点他也知道。于是她便独自睡在斗室(at-tic)中,在一张窄床上。
有一些同学认为窄床代表着达洛维夫人的同性恋倾向,她无法接受与丈夫理查德的肌肤之亲,所以宁可称病独处,尤其在这一段中,达洛维夫人谈到了女人之间的相爱;有一些同学认为窄床反映出夫妻之间的渐行渐远,丈夫称她有病就与她分房而睡,而她也把两人的疏离包装成了相敬如宾,甚至,她可能是性冷淡——“就由于那种冷漠的性情,她让他失望了”;另一种解读则把床视作了棺木,结合充斥在这一段中的衰老与死亡的焦虑,他们认为越来越窄的床意味着越来越短的生命,窄床因而又与滴水的龙头、烧剩的蜡烛属于同一类意象。
在课堂的阐释讨论中,经常会出现“孤证不证”的现象,就是仅仅靠自由联想把某个意向对应到一个解读上,但在文本中乃至文本之外找不到佐证。比如看到“一双黑眼睛”,就觉得那代表着生命力与欲望,可是,凭什么这么说呢?理解文学时,仅仅有感受和联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说服力的证明,至少是用更多的类似表达来验证自己的判断,使其不仅仅停留于一种简单的、一次性的印象式批评上。我常常采用的方式是“平行对读”,在文本之外找同类或者相反写法的支撑。所以,在讨论结束后,我又补充了几个例子:若要论床代表婚姻的和谐,可以引用史诗《奥德赛》中那个在橄榄树之上建成的婚床,它不可移动,象征着床对婚姻持久与忠贞的祝福 [1] ;若要论床代表婚姻的淡漠,可以引用海明威《雨中的猫》里那张始终只有丈夫躺着的床,他的卧床懒起,他的漠然于妻子的求助,都暗示出两人婚姻关系的崩溃;若要论床代表生命的虚无与终结,例子就更多了,因为人们在床上度过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说是老于床上甚至最后死于病榻的,那么可以从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开始讲,她为我们捕捉到了一个恐怖的瞬间:“皱起的床单证明了我们夜夜与虚无交媾,夜夜不在。”
很多时候,文本细读被误认为对着一部小说死抠字眼,但只读一本书是连那一本书都读不好的,反过来说,要读好一本书,可能需要读十本百本书作为辅助。文本细读有一个潜在的必要前提:贪婪的泛读,这样,才能把泛读到的东西吸纳成解释和支撑细读内容的材料。同时,一部作品写得再好,也不会在逐字逐句的单调释读中释放其全部魅力,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只有放置在整个文学传统中,加以生活经验的印证,才能真正被判断。所以,我作为一个文学的阐释者,同时也是教学者,更倾向于让一部作品在万千作品中彼此碰撞与激发,正如我和学生们的碰撞与激发一样。
华东师大的罗岗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泛读和细读互相支撑的例子,我也经常在课堂上引述。大家都很熟悉《孔乙己》中孔乙己被打断腿的情节,因为他偷了书,但是偷书何至于此呢?其实,据罗老师推测,有可能他偷的是宋版书。在中国印刻史和书籍史上,有“一页宋版书,一两黄金价”之说,因为宋版书流传不多,加以宋代刻印的书籍内容近于古本,刊印精美,成了后世藏书家追捧的对象。如果不了解这段书之外的刊刻史,其实就不明白为何偷了书要被打断腿。使用历史文献的泛读辅佐细读,这也是更符合学术传统的一种实证的路数,如果你有兴趣翻开一本外国文学的学术期刊,会发现里面的历史文献内容可能还要多过文学本身的内容。
在外国文学的阅读中,读者既可以选择历史实证的方法,也可以选择文本之间更为文学化的对读——同样是讨论家具,《简·爱》中出现了红木架的大床,熟悉经济史的读者就不妨回忆一下马德拉岛和加勒比海地区红木枯竭的历史,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财富来源地。也就是说,作家在写作时不自觉地使用了当时英国殖民经济带来的社会变化作为故事背景。而《包法利夫人》中出现的桃花心木的床乃至棺椁,这又怎么理解呢?其实,在很多作品里桃花心木都被视为坏品位的代名词,它无须我们有什么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读得多了,“潜规则”也就慢慢领悟了。夏尔执着地要为死去的爱妻打造桃花心木的棺椁,只能再次暴露出他的俗气。
 对于非学院派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后面这种对读方法可能会更有趣一些,也更接近本能一些。
对于非学院派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后面这种对读方法可能会更有趣一些,也更接近本能一些。
[1]
诗中奥德修斯说道:
院里生长过一棵叶片细长的橄榄树,
高大而繁茂,粗壮的树身犹如立柱。
围着那棵橄榄树,我奠基起墙盖卧室,
用磨光的石块围砌,精巧地盖上屋顶,
再安好两扇坚固的房门,合缝严密。
然后截去那棵叶片细长的橄榄树的
婆娑枝盖,再从近根部修整树干,
用铜刃仔细修削,按照平直的墨线,
做成床柱,再用钻孔器一一钻孔。
由此制作卧床,做成床榻一张,
精巧地镶上黄金、白银和珍贵的象牙,
穿上牛皮条绷紧,闪烁紫色的光辉。
这就是我作成的标记,夫人啊,那张床
现在仍然固定在原处,或者是有人
砍断橄榄树干,把它移动了地方?(王焕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