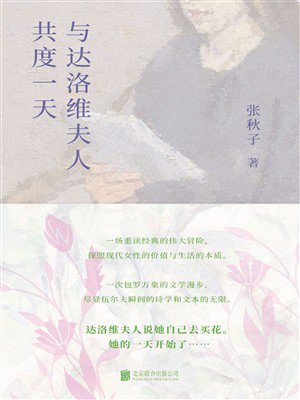4
回到我们的细读中,我也分神和离题了。
在这个细读部分中,无论是刚才说的床、阁楼,还是家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包裹感。在比较空旷的房间里待着时这种感觉就不太明显,但是冬天窝在被子里,被包裹的状态就很具体了。而且,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身体的被包裹感,但是很少注意到心灵的相对体验,我们来看看克拉丽莎准备上楼前描述的自己的状态:
恍惚自己在户外,在窗外,悠悠忽忽地脱离自己的躯壳和昏昏沉沉的头脑。
这段话很有意思,它一方面说明克拉丽莎是在屋子里,被物理房间包裹着,另一方面则说她感到心灵被躯壳和头脑包裹着。因此,她想开个小差,跑到户外去。读者似乎能感觉到,无论是家宅家具还是身心,都像腔体一样束缚住了达洛维夫人,她则做出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动作:频繁地关门开门、开窗关窗——就好像一个被禁锢在某个腔体或者空间中的人,在逃逸与开小差的边缘试探。哪怕在走上楼的时候,伍尔夫还交代了一笔:“在窗前停留了片刻。”
推开窗户、推门出去游荡,几乎都与对居住在空间中的自我的开小差有关。它以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代表了人对逃脱当下环境的渴望,通俗来说就是“换一换空气”。我的一位学生今年考研失利,很痛苦地坐上了地铁,想让地铁载着自己没有目的地前行,后来丧头丧脑地走出地铁口时,“忽然感到风是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根本逃不掉”。他向我描述说,那一瞬间他忽然从痛苦里抽离了出来,开始感受起这股挺邪门的风,因为开小差,一时间竟然忘了自己有多难受。走出地铁口,也有点像推开门窗,人被裹挟着他的强烈情绪释放了片刻。
我对“门”“窗”的兴趣来源于纳博科夫的启发(后来读了齐美尔的哲学随笔《桥与门》后,发现“桥”也可成为一个大作文章的意象)。英国文学中的窗子,本就是充满了历史悖谬的意象。英国历史上曾有一种奇怪的税叫作“窗户税”,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征收,一栋住宅有七扇以上的窗户就得纳税,人们得为阳光与新鲜空气付款。越是有钱人家,宅邸越阔气,被征的税也就越多,直到1851年这个税种才被废除。英国文学里也没少出现关于窗户与金钱花费的主题。在课堂上讲授后,我注意到同学们对这套隐喻模式的学习和运用非常快,很快,连潘金莲推窗掉落竹竿的情节也没逃过被大家阐释的命运——她对自己无奈嫁给武大郎的命运有着强烈的不甘,推窗也就有了一丝开小差、逃离痛苦婚姻的意味在。
在伍尔夫的小说中,推门推窗与走神的关系被处理得更为复杂一些,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不是说她一旦开窗,就是打算走神去想点别的什么,或者打算开个小差。大家可以想象,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是站在门槛上说的,她要游离出居家禁锢的生活,这是一种指向逃逸的开小差。但是,当她推开花店的门时,她又进入了一种专心购物的情绪中,直到窗外车辆发出的爆响使她再次分心。门与窗的开开关关,使她在分心与专注之间来回滑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心不在焉的写法,伍尔夫并不想将某个意义绑定在对应的某个开门推窗的动作上,而是让意义在门窗的开开关关之间来回摇曳。伍尔夫似乎相信,人的处境乃至身份会决定做同一件事是分心还是专心。
这非常容易理解。比如在课堂上,我发现一个学生在玩《英雄联盟》,那相对于我的课堂来说他就是在分心,但是对于他手里的游戏来说,他却非常专注。我们甚至可以遥想,在十八世纪小说兴起于欧洲大陆后,一个女仆如果躲在阁楼里看书就是在分心(女仆其实是当时崛起最迅速的阅读群体),可是她的女主人在卧室的床上读书却是专心。契诃夫在中篇小说《文学教师》中提供了一个三角形的分心与专心的循环,他让读者判断一个人的专心与走神是怎样在感情的锁链上发生了滑动。《文学教师》中有一场发生于晚宴之上的三角恋。当一个军官慷慨激昂地向大家讲起自己的作战经历时,暗恋他的女人“正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眼也不眨,仿佛在想什么心事,或者是想得出了神似的……”而暗恋这个女人的男人也没有在聆听,他也分心了,他观察着女人,心中充满痛苦。男人和女人似乎都专注于自己的情感体验,却也都偏离了听故事这件正事。整个故事也就此在分心与专心的流动中运转了起来。
在《达洛维夫人》全书最后的高潮晚宴中,伍尔夫两次写到窗子没关上,窗帘被吹拂起来的场景:
橙黄的窗帘轻柔地飘拂着,上面绣着天国的仙鸟,也在飘扬,仿佛振翅飞进室内,飞出来,又缩回去(因为窗子打开着)。
每次出现这个窗户的场景,读者就会发现叙事的焦点转变了,本来作家在讲着这个人物的事情,忽然写到飘飞的窗帘,似乎心绪也被轻盈地吹了起来,马上又开始说另一个人的事。单一的焦点被吹乱了。
 也就是说,其实小说中的分心不仅涉及故事层面的分心——人物是如何通过开小差来逃避、自我保护或者呈现心灵的丰富性的,还涉及讲故事的层面——也就是叙事层面的分心。
也就是说,其实小说中的分心不仅涉及故事层面的分心——人物是如何通过开小差来逃避、自我保护或者呈现心灵的丰富性的,还涉及讲故事的层面——也就是叙事层面的分心。
叙事如何分心呢?传统文学在描写一件东西时,观察的位置大体是固定的。比如我要描绘一个苹果,颜色大小形状,大体会从一个视点出发,不会一会儿钻到苹果核里写,一会儿又从苹果里肉虫的视角来写,一会儿再从离苹果十万八千里的远方写。可是,来看看下面这一段,这是所有人在摄政公园里时,突然看到天空中飞过一架飞机时的情景,这位登普斯特太太也是驻足围观的一员:
啊,瞧那架飞机!登普斯特太太不是总想到国外观光吗?她有个侄儿,是在异乡的传教士。飞机迅速直上高空。她总是到玛甘特去出海,但并不远航,始终让陆地呈现在她视野之中。她讨厌那些怕水的女人。飞机一掠而过,又垂下飞行,她害怕得心都快跳了出来。飞机又往上冲去。登普斯特太太吃得准,驾驶飞机的准是个好样的小伙子。飞机迅捷地越飞越远,逐渐模糊,又继续往远处急速飞行:飞过格林威治,飞过所有的船桅,飞过一栋栋灰色教堂,其中有圣保罗大教堂和其他教堂;终于,在伦敦两边展现了田野和深棕色树林,爱冒险的鸫鸟在林子里勇敢地跳跃,迅速地一瞥就啄起一只蜗牛,放在石块上猛击,一下、两下、三下。
在课堂上,我邀请大家判断,这么短短一段话里,出现了多少种观看的视角?这一段话全都是写登普斯特太太所看到的吗?显然,一开始是她,她在仰视,想起了自己当传教士的侄儿;接下来,其实就是进入飞行员的视角里,因为只有由他从万里高空俯视,才能遍览大地上的船桅、教堂与森林;至于最后一句,可以当成是一个无名的观察者,他拿着放大镜,从天空之高一下子拉近到草木之深,让蜗牛纤毫毕现。假如伍尔夫扛着一架摄像机在拍摄画面,估计她一会儿给一个远景,一会儿又会从飞行员的角度给一个主观镜头,一会儿拉近焦距,微观拍摄地面场景。
她的观察视角是分心的,不是专心的,是走神的,不是“固定机位”的。我很喜欢伍尔夫在这段“炫技”中展现出的想象力与充满野性的本能,她放弃了现实主义教导的种种规则,她发现自己除了本能与想象之外,不允许有其他的指导。她让我想到塞尚的画作,那种允许自己的画笔与颜料向各个方向扩展,而不是把它们限制在画布的某个部分的力量,塞尚同样是赞美“失焦”的。当然,文学对伍尔夫的回应更为丰富。在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有一段对于街景的描写令人直呼过瘾,作家同样使用了分心的手法。伍尔夫的分心偏向于观察的远近变化以及观察者身份的变化,但德布林则偏向于在人的时间尺度上滑行和四散:
在洛特林大街站,有四个人刚刚上了4路,两位中年妇女,一位忧郁简朴的男子和一个头戴软帽及护耳的小青年[……]年纪较大的那位,买条腹带,因为她生就了爱得脐疝的毛病。[……]那位男子是马车夫哈则布鲁克,他的痛苦来自一只电熨斗,这是他替他的老板买来的便宜旧货。人家把一只差的给了他,老板才试了几天,这玩艺儿便怎么也通不上电了,他得去换一个,那些人不愿意,他这已经是第三次坐车去了,今天他得再加付一点钱。那小青年,马可斯·卢思特,后来成为白铁工,另外七个卢思特的父亲,加入一家名叫哈利斯的公司,安装,格绿老一带的屋顶维修工作,五十二岁时在普鲁士分组抽奖中中了四分之一彩,不久退休并在要求哈利斯公司给予补偿的诉讼期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他的讣告内容将是:我挚爱的丈夫,我们亲爱的父亲、儿子、兄弟、姐夫和叔叔,保尔·卢思特,因心脏病突发,于9月25日逝世,终年还不到五十五岁。
(罗炜译)
为什么说这一段话精彩至极呢?
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固定的观察角度描述4路公交车上的几位乘客,却把不同乘客的过去、现在、未来合并到了一段里来写。那个女人的过往,是从小就得了脐疝的毛病,而那个男人,现在正要去给老板换货,最后一个小青年,则被告知他日后的命运乃至讣告。在这个了不起的段落中,德布林的分心体现在时间感的分心上,他让时间的箭簇从过去、当下、未来三个方向射出,然后,全部插到这辆4路公交车上,每个人的生命秘密也都在这一刻交汇。伍尔夫与德布林的天才都在于,当读者已经预设了小说画面的稳定和静止时,他们戳破了画布,扭曲和扩展了小说中的时间与视角秩序。
这种时间和视角的扭曲、扩展是极为现代的体验。就拿这个细读章节中飞行员俯视大地的视角来说,在古代就不可能出现,传统作品中会有从鸟的视角俯瞰大地的描写,但多半是作家们在登山后,假借鸟眼实现的。比如《荷马史诗》里写“太阳的亮光收入长河,引来黑夜,覆盖盛产谷物的田畴”,或者中国诗歌里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等。但是,只有在飞机发明之后,人们才真正第一次亲临天空,小说中也会大量出现舷窗中的景观。海明威在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描述了飞机一飞冲天时,地面的景观从立体变得扁平的过程,斑马、角马纷纷变成了黑点,直到那时候,他说自己才开始理解毕加索等人的“立体主义绘画”了。现代机械使得人对距离、时间的感受都发生了变化,从哈勃望远镜到电子光速显微镜,无不在改变着人的认知。
可以说小说在二十世纪出现对静止画布的扭曲与戳破,是一件必然之事。
关于文学的分心,我最后想说的是,读者们大可以在阅读《达洛维夫人》时分心,这是一部欢迎分心和走神的小说。
我的学生们普遍反映了“读几页发现白读,又翻回去重新开始”的走神经历。同时,这也是一部打碎“思维导图”的作品,确切地说,任何一部好的作品都是拒绝思维导图的,它们更欢迎停顿、混沌与混乱。至于我自己,想到现代社会中“专注暴政”里可能暗含着的强力意志,也就对坐在教室第一排大玩手机的女孩不那么气恼了,当然,如果她在一学期专注玩手机的过程中能分心看看我,倒也是我乐于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