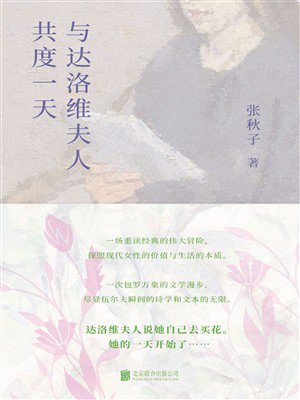1
2022年秋天,与几位毕业的学生聚会,天色已晚,我寻思让一位住在外地的学生留昆住一晚,她很紧张,那时还没有“解封”,她担心第二天一起床就无法离开昆明了——万一行程码变红了呢?她开玩笑说,我们都变成“临时性的人”了,安全也只是“临时安全”,就好像那个叫作“糖豆人”的小游戏,主角必须一刻不停地跳到下一层楼梯上,否则,脚下的楼梯就会消融,无立足境。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深深俘获了我们,它规定了人的行为与选择,而且,它还变得越来越快。
同时,人们似乎也无法忍受慢了。慢意味着等待,手指频繁戳着电梯的“关门”按钮,它多少减缓了自动关门之前等待的烦躁;慢意味着被按在座位上,但当飞机落地还在滑行时,大家都已经站了起来;慢意味着颗粒感与摩擦,但手机键盘已经被智能机的平滑界面所取代,指腹不再需要与凸起的字符较劲,说不定打字时又节省了好几秒。一切都在顺从我们变快,我们则被掠夺了耐心。
可是,文学偏偏是从慢里诞生的。
纳博科夫有一篇令人惆怅的小说叫《仁慈》。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是个雕塑家,被塑造成了一个软弱被动的形象。他正经历着一桩失败的爱情,对方嘲弄他、背叛他。男人本来约好了要与女人好好谈谈,可是久等她却不至,站在柏林城墙下两根孤零零的柱子中间,男人终于决定结束等待,他甚至告诉自己:我想从你身上找到的欢乐也不一定只隐藏在你身上呀,世间万物都有呀,这就是“仁慈”嘛。他坐上有轨电车回家,却只听得车顶“砰”的一声。
那是风吹落的栗子轻轻砸在了车顶,又顺着车厢滚了下去。男人开始谛听起来。过了一阵,“砰”的一声,过了一阵,又是“砰”的一声……
小说就这样结束了。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没法给小说设置“倍速播放”而干着急,不然就可以加快栗子掉落的速度,然后看看最后发生了什么。可是,纳博科夫只是慢悠悠地写栗子一个个掉落,并没有什么“大结局”。其实,当男人在谛听的时候,纳博科夫悄悄告诉我们,他还是不死心,还是不甘心女人对自己的爽约,之前那些关于“仁慈”的说法统统是自我安慰,他默默地等待着栗子掉落,就像默默等待着女人回心转意。所以,栗子只能慢慢掉落,它把男人的等待与痴心拉得像一根游丝般细长,却总也剪不断。也是在这时,文学的美妙到来了。它逼迫我们拾回耐心,好好想象荷马是怎样走街串巷、经年累月记录歌谣的,好好想象福楼拜是如何不断逼迫自己、用三个月写出一段话的。
这也是我想与学生们共读《达洛维夫人》的根本原因:我们对待自己的生活太过草率和轻忽,几乎没有一刻停下来,细数今日的每个片段,好像完全忘了这些时刻是一去不回的。以至于,填满一天的方式和填满十年没什么区别,抛掷这一刻和抛掷这一生也差不多。可是,《达洛维夫人》居然可以只讲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一天时光!这里面有一种郑重其事的贪恋,它恰恰是我们对待生活漫不经心的态度的反面。
在伍尔夫的日记中,她谈到过这种贪恋痴迷,她的日子照样是“一天天地过去了。有时我自问是否被生活迷住了,一如孩子痴迷银色的星球一般,这是否就是生活?”。于是,她决定把这个星球捧在手中,“静静地摩挲,它溜圆溜圆,沉甸甸的”。因为把玩许久,甚至被包浆,具有了某种永恒的气息。同样的,在《达洛维夫人》中,文学以特有的迟缓让人们悬浮在自己的思绪中,忘了往前迈步。
《达洛维夫人》是反速度的,是缓慢的。
有时,我甚至疑心,这种反速度背后藏着作家对速度的终点——死亡——的深深恐惧。她要通过截停和放大每一个细节,推迟终点的到来,就像福克纳笔下的昆丁,通过把手表摔碎,推迟死亡与溃败的到来一样。毕竟,任何一个读过伍尔夫日记和小说的人,都会被她深切的死亡忧虑所击中。如果你恰好也暗藏着类似的恐惧(时至今日,我仍然会在午夜被自己要死这件事突然吓醒,有如坠深渊之感),那么你也许就会体察到伍尔夫作品的底色,那是贪恋与恐惧的交织。于是,对伍尔夫来说,写作的行为,逐渐变成了一种驯化时间与对抗死亡的可能,对读者来说,阅读的行为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得放慢速度,迟缓细读。
这是读者能对一位作家回报的最大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