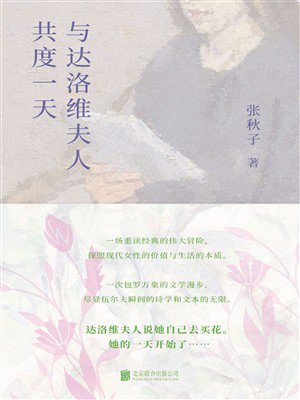2
小说的开篇在文学史上极为有名,它正是对一个瞬间反速度的抓取:
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
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太没头没脑了!它把整个文学传统给掀翻了。
普通读者期待着作者亲切又絮叨地交代背景知识:达洛维夫人是谁啦,她多大年纪啦,眼睛是什么颜色啦,为什么要去买花啦,等等。总之,那些关于主角的身份与历史信息就像蛋糕上的奶油,堆得厚厚的,吃起来才够味。可是,伍尔夫的笔像一柄冰凉的细刀,无声快速地切入蛋糕,把所有腻歪的奶油裱花都抛诸脑后,直接将这个叫作达洛维夫人的人生命中的一个侧切面冷不防地端给了你。
这种甩掉包袱的写法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塞林格在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里蛮可以轻松地说,你们可别指望我去聊什么出生、家庭、父母职业这些“故事式的屁话”,但倒推三十年,这么写就暗含着一种挑战读者阅读习惯的勇气。以至于,哈代来伍尔夫家做客时,有点抱怨地说:“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改变了。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小说总得有个开头、中间和结尾。我们相信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可是现在倒好,有这么一个故事,竟然以一个女人走出屋子而告终。”这种写法上的变革非常具有现代意味,它暗示着作家将穿上“紧身衣”,把历史、传统乃至时间的赘疣全部割掉,更加轻盈地挤进现代世界。
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倾向于将漫长的故事掐头去尾,只把生命中的某个片段逮住,然后放大它,观察它,将它封装在琥珀中赏玩。人们总说时间如水,仿佛它在平面上滔滔不绝地流过,但小说家改变了时间的水平属性,让它变成了停顿的垂直形态,不断在一个动作、一个状态中往深处扎根,于是,事情的模样改变了。日常生活里,咱们上几节楼梯不过就几秒钟的事,但是,同样是上楼梯,作家的时间单位则放慢到了毫秒,也即一秒钟的千分之一。比如科塔萨尔在《上楼梯指南》这篇古怪的小说里,煞有介事地为读者介绍了怎么上楼梯:
上楼时一般应面对楼梯,因为侧身或背对楼梯进行将产生相当程度的不适。正常的做法是采取站姿,双臂自然下垂,抬头(但不要过分抬头以至于眼睛看不到下一级台阶),呼吸须平缓而规律。上楼梯应从抬起位于身体右下方的部分开始,该部分一般会被皮革覆盖,除个别情况外其大小与台阶面积吻合。该部分(为简便起见我们将该部分称作脚)安置在第一级台阶上之后,抬起左边对应的部分(也称作脚,但请勿与此前提到的脚相混淆),将其抬至与脚相同的高度,继续抬升直到将其放置在第二级台阶上,至此,脚在第二级台阶。
(范晔译)
我在阅读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脑补了一出上楼梯大戏,目光与知觉追踪到了每一个动作的细枝末节之处,我开始尽情地想象:手臂垂到哪儿?皮革覆盖的部分是什么感觉?膝盖应该抬得多慢?就像在做瑜伽时,人们被提醒注意自己的呼吸,放松感要从脚趾蔓延到小腿、从腹部到头皮,放慢的文学同样延长并超越了普通的感知,人们三步并作两步上楼时所遗漏的、所放弃的,被放慢的文学一一捡起并耐心还原了。
在这些时刻,作家们有一种完全违背功利主义的较真,不仅让我们在阅读中重构时间本身,更逼近了那些大家习以为常的动作与形态的内核,而我相信,事物的内核总是独一无二的。中世纪神学家斯科特斯有个很美妙的拉丁词叫作“Haecceity”,翻译成英文更好理解一些,“thisness”此性,就是这个东西有而其他东西绝对不会有的特性,只存在于此物之中的特性。假如在一部小说里浮皮潦草地写主人公看到了很多花,那么这个“花”还是抽象的、模糊的、没有特性的花,然而,伟大的作家是不会笼统地写“花”的。我常常惊讶于普鲁斯特世界里的精细:没有共相,只有具体,没有模糊,只有“thisness”,“花”变成了菖蒲花、葛兰花、龙须菜、勿忘我、椴花、凤仙花。在《达洛维夫人》中,“花”是同样具体的:翠雀、香豌豆、紫丁香、香石竹、三尾鸢……在这些时刻,物本身的独一无二性引导读者进入了一个颜色、气味、姿态都确凿的世界,甚至,它们以前是从哪个国度与地区引进的,以后的花期又能保持多久,也都一一变得真切了,事物不再是眼睛匆匆一瞥就滑过去的背景,它们被拽出了隐形的状态,浮现出特殊的轮廓。我以前读武侠小说,总看到“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说法,那么读文学大概就是“天下文学,唯慢不破”了。
想来,文学的魅力正在于使一个放慢乃至凝固的瞬间里饱含了关于过去与未来的所有可能。
在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伍尔夫知识的背景下,同学们对这句话展开了讨论。迎面而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句话说的是“达洛维夫人”而非主角的名字“克拉丽莎”?进一步地,为什么小说不取名叫《克拉丽莎》?参与讨论的同学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意识到,达洛维夫人是克拉丽莎嫁人以后的社会称呼,是一种公共身份的指认,而克拉丽莎则是闺名,是她私人自我和本真自我的体认,在这两者之间,主人公应该更在乎面向公众的自我呈现,也就是嫁给了达洛维后的妻子身份。就像在《红楼梦》里,我们也看不到男性仆从妻子的名字,她们的称呼被丈夫的名字整个地覆盖住了:周瑞家的——指的是周瑞的老婆——赖大家的、林之孝家的,等等;或者现在的很多女性,自我的称谓被孩子遮蔽掉了,她们的名字变成了淇淇妈妈、聪聪妈妈或者更笼统的“宝妈”。大家的这个观察很重要,因为这对后文理解克拉丽莎的许多行为有着决定性意义。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伍尔夫要用这个书名和这个开头暗示我们,对于女主角来说,她的本真自我在故事开始之前与开始之时,就被先行遮蔽掉了?
可是,这句话里又有不那么平顺的地方。原句是“Mrs.Dalloway said she wouldbuy the flowers herself”,这似乎暗示着,女主角以往总是有人替她买花的,她大可以事事让他人代劳。但刻意强调“自己”,就把买花的主动性强化了,是她自己,而不是他人,被推到前台,凸显、放大。这也是整篇小说的主题之一:人如何塑造自我、求索自我。这让人联想到伍尔夫那篇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 A Room of Her Own )里,也采用了这种刻意强调的口吻:“own”。我们似乎看到一组矛盾渐渐浮出水面,这个女主角似乎想强调自我,但真实自我的身份又被已婚的社会身份遮蔽了,那么,她总体上应该是一个很拧巴和纠结的状态,在出世和入世之间不断摇摆,很快,我们就会在后文的讲述中验证这个推测。
也就是说,这一个动作的瞬间,对主角过去的经历与未来的渴望都有所提示。
在细读文本时,不妨掂量作家们采用的小小词汇。因为,词汇本身就是有质地、有软硬、有大小的,诗人张枣甚至认为(汉语)词汇是有甜味的。以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为例,主角巴特比对于一切超过他本职工作范围的要求都一概回绝,哪怕只是顺路跑个腿,他的态度都极为强硬,以至于最后被送入监狱,死于其中。麦尔维尔想通过巴特比这个伟大的形象,塑造一个不计代价、敢于拒绝的人,毕竟在现实生活里,大家更多的是言不由衷的接受与同意。按照惯性的预设,这么强硬的人说拒绝的话,大概率会撂下狠话,在中文译文中,他的口头禅是“我宁愿不”。如果不读原文,读者大概会猜测他说的是“rather not”,这个词有一股子决绝的味道,但其实,巴特比说的是“prefernot”。“prefer”(宁愿、更喜爱)这个词则有某种选择的意味,好像我可以选这么做,也可以不选,但是,当我们有得选的时候却仍然选择了“正确”而非“舒服”,这反而使得“prefer”有了更压抑住的、未曾言明的孤勇。
此处,麦尔维尔通过一个看似弱的词来表达强悍。
作为中文读者,我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译文,如果有机会对比原文词汇的选用,往往会有意外之喜。我在读乔伊斯的《泥土》时,一开始以为泥土是常见的“soil”一词。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描写泥土的场景,但是让女主角在玩爱尔兰的占卜游戏时,蒙着眼睛摸到了一块又软又湿的东西,周围顿时响起了窃窃私语,人们说起了关于花园的什么事情,还说要把这个东西扔出去。如果中文读者以为这块东西说的就是来自花园的“soil”,那么故事就会变得很“实”,失去了某些不确定的模糊之感。我在课堂上讲这个小说时,大家一致的反应就是,女主角捏到的肯定是泥土,标题不都告诉我们了嘛。大家也会接受对泥土一词最常见的联想:它代表死亡,女主角很快就要入土了。可是,死亡的主题对我们理解女主角没有什么意义,谁不会死呢?
其实乔伊斯用的词是“clay”,在英文里它既有“黏土”的含义,又有“肉体”和“类似于黏土质地”的含义。模糊多义的词汇为我们打开了更为丰富的理解空间:如果,女主角摸到的是一块丢弃在花园里的肉,是否意味着她对肉体的内在渴求?小说多次提到她对结婚的关注,而且她在路上还因为对一位绅士遐想联翩丢了蛋糕;如果,女主角摸到的是她丢失的那块蛋糕(有可能落在花园里被弄脏了),是否意味着她总是在经历丢失与匮乏?小说里的人总在丢东西,不是丢了胡桃夹子,就是丢了蛋糕,要么丢了过去的恩情,人们普遍处于巨大匮乏与丧失之中。总之“clay”一词比“soil”传递出更丰富的可能,这也需要读者花多一点的时间去找找原文,比对比对。
好的作家肯定总是词语的炼金术士,哪怕是最寻常最乏味的词语,在他们的笔下也会像一枚落入深井的石子,激荡起深刻的共鸣与回音,所以,无论是《达洛维夫人》还是别的文学作品,我在进行细读时常常想要把一个词、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写法后面的隐喻搞清楚。因为文学归根结底是关于隐喻的艺术。它如同一枚蜂蜜味的瓜子,故事情节只是壳,意义则藏在果仁里,如果我们像不会嗑瓜子的孩子一样,只是吮吸一下壳上的蜜味儿就将其丢弃,未免可惜,更好的吃法是带着壳的滋味嚼碎果仁,让甜与香混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