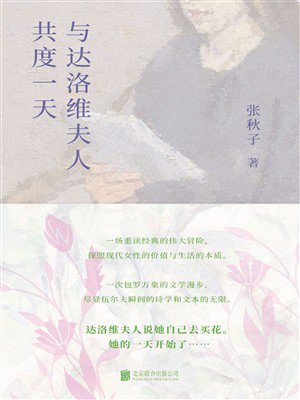3
小说的第一句话饱含着瞬间的诗学,它一下子就传递了一颗心、一个人、一件事的秘密。也正因为它是对瞬间的抓取与放大、停滞与摸索,所以这一句话可以继续讨论。
——它是怎么说出来的?发出声音来了?抑或是内心独白?跟谁说呢?女仆露西还是她自己?也就是说,这句简单的开场白里,包含着很混沌的东西。这也是小说与电影或者戏剧不同的地方,所有的声音都不是直接让人听到的,都需要“脑补”,而读者们之所以对这种声音的混沌不敏感,是因为太过于把小说当成一种信息和内容来理解,忽略了它本身也是一种修辞,内容如何被讲出来也是重要的。
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读者经常会被作者施的魔法拖入情节的旋涡里。这就导致课堂讨论时,大家常常会忘记是在读一部虚构作品,而是把情节当成了现实来争论。我的学生们为《罪与罚》中马美拉多夫到底是不是“人渣”争论过,为《红与黑》里于连最后忏悔时对贵族的诅咒是不是真的争论过,还为《达洛维夫人》中彼得与克拉丽莎两人是否“意难平”争论过。假如把这些人名与书名抛开,大家看上去简直是在聊班里最新出现的八卦或者最近爆出的社会新闻。但是,在讨论内容与情节时,始终需要留出第三只眼,以旁观的视角来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诱导了我们,让大家争论不休?
是作者的写法。
其实,很多时候,作者的写法未必会让人争论不休,反而会让人习焉不察,也就是把一些内容看成理所应当的信息交代。这种技巧更隐蔽,也更令人麻痹,读者看完后往往想的就是,哦,知道了。“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这句话起到的就是麻痹读者的作用,它仿佛在自我宣誓说:你们可别想多了。但文学批评做的就是“想太多”的活儿。有几次和一位毕业生在微信聊天时,注意到她特别喜欢这样的表达:“老师您能不能帮我看看《醋栗》呗(超小声)”“老师您去上课能不能把我带进学校里面(小声)”——这样的讲法会让我感到有两个人,一个人躲在另一个后面,冒出半个小脑袋,把她的心里话(通常自己不太好意思说的)通过前面那个人说出来。
当然,到这里,专业的理论家估计就该扯“隐藏作者”“叙事声音”“自由间接体”之类吓人的名词了,但我想到的是科塔萨尔在一篇极为顽皮的小说《剧烈头痛》里写下的极为顽皮的那句话:“一些句子爬到另一些句子上面。”当我看到与同学的聊天内容时,声音的交织与攀爬、人的多重面孔、闪躲与呈现,忽然就生动了起来。如果我们认同“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也是这样的表达,那么也可以想象,更多的句子从这一个句子下面爬了上来,更多的声音从这一个声音背后冒了出来:
有可能,它是克拉丽莎对女仆露西说的,因为后文交代,露西“已经有活儿要干了”。这像一句简单的信息传达。
也可能,它是克拉丽莎大声对自己说的,因为她需要给自己鼓鼓劲儿,她并不能全然沉浸在世俗世界中,她的心态多少有点欲拒还迎,这种心态决定了她的婚姻选择乃至人生。
还可能,它是克拉丽莎的内心独白,因而有了一丝不需要向外宣誓的笃定、一种沉思默想的气质,这与她后文展现出来的胡思乱想的气质是相符的,也反过来印证了她对世俗世界渴望的另一面:精神追求。
所以,谁在讲,讲给谁,怎么讲,这些问题很重要。它甚至会比直接给出的情节更能够暗示出人物的性格乃至命运。也就是说,当内容在大声嚷嚷时,形式在小声嘀咕。有时候,大家会有个错觉,怎么我听得出生活中别人对我的阴阳怪气、言外之意、隐约其词,但却看不出小说的类似伎俩?这是因为小说省略了日常对话中具体的语境、语气、音调乃至神态,只留下最核心的文字。它们以一副骨架的方式召唤着读者去填空,用他的神经、他的唾液、他的火花、他的想象、他的敏感——这当然是有难度的。有一次讲完这句话的课后,有个男生找我来聊。他说,读到小说的第一句话后,他就“琢磨了一下午”,还和朋友讨论了很久,因为他一开始搞不清楚说出这句话的人和克拉丽莎的内心之间的距离;又谈到,自己去读文学理论后似乎有点茅塞顿开,以至于他后来每读一段都要去琢磨,讲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隔得多远这个问题。需不需要用理论来理解文学,当然还是看个人的思考习惯,我会更偏向于非理论的理解方式,用个体的经验介入,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男生说自己“琢磨”的习惯。绝大多数人看完第一句话后就滑过去了,没有在寻常里咂摸到古怪,变成了常说的“习焉不察”,而琢磨就是“察”,它可能是阅读文学时最为珍贵的一种准备。
有了琢磨,就有了疑惑,也才有了解答的可能。
所有视角与声音的展开都是有意义的。今年春节假期,我帮助已经年近九十的奶奶整理完了她的回忆录。回忆录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1954年3月8日,一群少女在昆明圆通公园嬉戏玩耍,她们是即将奔赴工作岗位的白衣天使,我是班长,组织大家出来郊游,算是同学之间的告别。”这一句话里有一个明显的观看角度的转变,仿佛先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从远处客观地看着这群少女在嬉戏,我的奶奶也在其中,但是马上,“我”出现了,全知全能的客观视角变成了清晰的自我,故事的镜头仿佛从第三人称拉近,一下子变成了更为亲切的第一人称。我奶奶这么写的时候,肯定没有什么文学技巧的考量,是她的经历与情感让她不自觉地完成一次视角的变化:人在年老回首往事时,因为时间隔得太久远,总会把时光开端的那个自我当成一个客观的对象来描述,当成一个与当下的自我没有关系的人来描述。这就是我所说的视角的意义。
当然,文学家的讲述会比我奶奶的讲述更具有自觉的技巧意识,比如我们来看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来自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第一句话这么写道:
我们正在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几乎所有读者一开始都相信,“我们”是主人公夏尔的同班同学,因为交代得很清楚,大家正在一块儿上自习。但若果真如此,后文中,“我们”怎么会知道夏尔的拉丁语是本村神甫启的蒙,知道他父母不肯送他上学堂,甚至知道他母亲在一家洗染店的四楼为他找了房子?这些根本就是同班同学不可能知道的背景信息——你能说出你萍水相逢的同学或同事家住在哪个小区的几楼吗?所以,福楼拜赋予了“我们”一双流动的眼睛,它有时候钻到同班同学身上,有时候钻到作者身上,然后在第一章结束时神秘地消失了……流动的眼睛跟小说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呢?它为故事注入了一股灵活的气息,让我们无意识地接受了用每一个角色的眼睛来目睹整个故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包法利夫人》是一部被众人之眼环绕起来的小说——回想一下,小说中的人物是多么热衷于凝视吧!
为何要对小说的开篇如此较真?
现代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一个告别再出发,作家们多多少少都交出了控制人物的按钮,让他们不带赘疣地出场,至少,作家们想表达的是,他们并不想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所以,无论是从作家的眼睛,还是从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一个人。
于是,站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开端,当达洛维夫人正独自出门买花,她的兄弟们也零零落落地上路了:
“神气十足,体态壮实的勃克·穆利根从楼梯口出现。”(《尤利西斯》的开头)
“他站在特格尔监狱的大门前,他自由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开头)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
“K抵达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城堡》的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