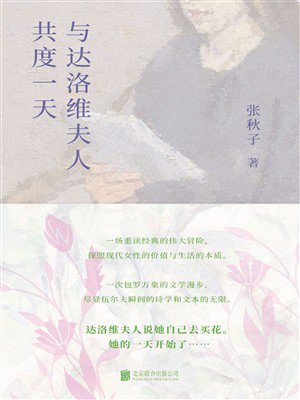2
在这个细读部分中,有两样东西压在了克拉丽莎的天平上:花和卷心菜。
在原稿《邦德街的达洛维夫人》中,本来写的是“达洛维夫人说她会自己买手套”,怎么后来变成了买花呢?消费社会中,购买行为带来了幸福感,有钱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各种仆从包围,而是被各种物质包围了。用充满世俗乐趣的购物开篇为整个小说中克拉丽莎的形象定了调:她的生命重力必然朝向“接地气”的那一面,朝向由购物与生活琐事组成的那一面,不然,伍尔夫完全可以在开篇写她在祈祷、阅读或者沉思,而不是多次写到她徘徊于橱窗之外,目睹玻璃后面混在一起的必需品与过剩品。这就是我说的生命的重量,它是一个人所有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个,它也是面对一道MBTI人格测试题时,犹犹豫豫或者毅然决然,你最终总会选择的那个选项——一个i人永远不会选择e人的选项。
进一步来说,手套是死物,是人造品,花则是有生命的,是活物,或者说,花曾是活物。手套会产生隔绝感。与伍尔夫差不多同时代的恩娜·谢泼德在游记《活山》中讲过一个细节,当她要去登山时,一位魅力十足的贵妇要求她把手套放下,不要带出去,因为“你的手不需要这些东西,许多力量只有通过双手才能来到我们身上”。手套隔绝了自然。我在侍弄花草时,一开始也会小心翼翼戴着橡胶手套,但它剥夺了手指的灵活性,让手上的皮肤无法呼吸,所以,我干脆把手套一丢,开始徒手接触土壤,只有在这个时候,土壤的湿润感、根茎的粗糙感才会涌到手上。也许正因此,伍尔夫打定主意把手套换成花,花暗示着购买者克拉丽莎的生命力。毕竟,花是伍尔夫最喜欢的文学意象之一,光“玫瑰”就在她笔下出现了250次之多,直到现在,仍然有她的粉丝热情地为她建造植物学网站,收录她所提及的各种花卉。
从手套到花,这一处微小的改动表明了作家的决心:她要把生命活力锚定在克拉丽莎的身上,她必须活下去,这也是小说最终的结局:她确实活下去了,而另一个主角赛普蒂默斯代替她死去了。小说中的重量不仅会藏在微小的改动中,也会藏在文本里那些看起来突兀、怪异的细节中,它们如支棱起来的胳膊肘,冷不防地捅了捅读者,引发注意。
在舍伍德·安德森的《母亲》中,儿子的全部生命重量藏在一张书桌里,它是儿子房间里的那张“由厨房餐桌改成的书桌”。为什么非得强调是餐桌改成的书桌呢?因为这张不起眼的桌子标志着精神追求与庸常的分道扬镳,当母亲还沉溺在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时,儿子已经开始探索母亲所不能理解的精神世界,这样一来,小说结局儿子的出门远行就是必然的。在《包法利夫人》中,艾玛的全部生命重量藏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那是艾玛还在修道院读书时看到的一幅画,画的内容无非是符合她浪漫想象的男女缱绻,青年男子抱着一个白衣少女。可是,福楼拜多写了一笔,说“女郎的腰带上还挂着一个钱包”——一个钱包出现在爱情画里是多么突兀和煞风景,福楼拜偏偏要通过这个看似扎眼睛的钱包告诉我们关于艾玛生命重力的全部秘密:她再怎样陶醉于情欲轻盈的欢愉,最终都会死于沉重的经济变故。
花在整部小说里处于动态之中。
小说有四次写到买花行为,每一次都使得花更接近于凋敝、脱离土壤、隔绝自然的状态:第一次克拉丽莎去买花时,花刚刚摘下,在马尔伯里花店里姹紫嫣红;第二次是雷西娅去买花,她从穷人手里买下来,差不多都快凋谢了;第三次则是理查德买了一大把花,却包在“薄纸”里,彻底隔绝了土地与自然。花本来是伍尔夫最喜欢的意象之一,它深深代表着她的生命渴望,但三次买花的递进结构却让死亡的气息逐渐增强,最后指向了文末赛普蒂默斯的自杀。显然,文学不一定模仿生活,但总是在模仿死亡,当这个幽暗国度没有给人类提供任何概念时,文学会主动用具体的意象为它赋形。有时候,一个很小的意象就足以揭示人类全部的幸福和需要经受的痛苦,就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少年人右侧臀部裂开的伤口,既像一朵玫瑰,又涌动着蛆虫,既昭示着死亡,又召唤着治愈。
所以,花被摘下,为消费的世俗快乐带来了一丝犹疑,因为它会很快枯萎、败坏,与世俗的物质痴迷构成正反面的死亡也正是在此时入场了——克拉丽莎从一开始就“预感到有些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也就是说,花在标记克拉丽莎生命的世俗乐趣与活力时,也在预告不祥,另一位主角的自杀其实在小说的第一页就埋下了伏笔。
做文本细读的时候,最需要留意的就是重复出现又微不足道的意象。包藏作者苦心的重复意象是一种文本中以小博大的嬉戏,它们往往会用最轻盈的形态激发出最具有牵引性的重力。《包法利夫人》中也有一个不起眼的物件,那是一座神甫诵经的石膏像,福楼拜一共写了它四次。最初是在女主角艾玛新婚典礼上出现,仿佛是在祝福她的婚姻,但随着故事推进,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破败。最后因为在搬家时车辆颠簸,它掉了下来摔得粉碎,艾玛此时对婚姻的忍耐也走到了终点,最终选择了出轨。也就是说,这尊石膏像为不可见的生命重力赋予了形态,让我们得以追踪艾玛婚姻状态急转直下的轨迹。每一年细读《包法利夫人》的课堂上,这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挖掘点,当一位同学得意地分享着自己反复阅读捕捉到的石膏像细节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被他的兴奋所感染,那不啻勘破一桩小小的密案。
自然,对于只读过一两遍的读者来说,这些细节太过于隐秘,难以察觉,毕竟人们在初读一部小说时,注意力大多放在接收信息上,只有事后反复琢磨,才能在接收信息的基础上处理信息。也有一些读者觉得,就算我没注意到买花或石膏像,也不妨碍我理解这些人下坠的命运啊,但是,也许这会多少失落一些切入文本肌理的快乐。会做饭的人都知道,盐是让食材吐出水分的好办法,萝卜茄子抹上一把盐,蔬菜的水分就会穿过细胞壁渗透到盐水中,食材也就会变得更加紧实。对于文学的阅读者来说,自己的手里也需要握一把盐,与文本交换,让文本吐出秘密。
再来说卷心菜。
克拉丽莎第一次回想起旧日恋人彼得时,表述得很有意思。她谈起关于他的过往,说都已经烟消云散,但是偏偏记得他说的关于卷心菜的话——“我喜欢人,不太喜欢花椰菜(cauliflowers)”。不过,在克拉丽莎的回忆里,变成了那些“关于卷心菜(cabbages)的话”(有的译本中是“白菜”)。为什么偏偏只记得这句,而且还把花椰菜记成了卷心菜?细微的差别意味着什么呢?
记忆自有其意愿,它会删除、模糊、扭曲,但留下的肯定是人最珍重的东西。对克拉丽莎来说,和彼得聊了那么多话题,但是她只记住了跟日常生活有关的蔬菜,也就是说,老老实实过日子的愿望牵引着她的生命重力。伍尔夫有意把玫瑰与蔬菜安排在一起,在后文中她甚至描绘“它们被栽种在同一个花园里”,但克拉丽莎二选一的结果还是菜。而且在她的记忆中,尚带有花朵含义的花椰菜最后变成了再寻常不过的卷心菜,一词之易,让诗意彻底消失了,柴米油盐逐渐吞没了沉思。
毕竟,与缥缈的沉思相比,卷心菜是更有重量的。
小说中关于物质的描写往往有几个作用:它会为抽象的内容注入一丝实心的感觉,把寓言式的主题压实。我很喜欢看卡夫卡长篇小说里关于食物的描写:黄油面包、熏板肉、8字形椒盐脆饼、沙丁鱼油、小蜂蜜罐……它们会为整个小说扭曲恐怖的氛围涂抹上人间的气味。物质描写还能为整个小说构建一个不明显但是必要的背景墙,让人物的行动得到依托,背景得到解释,不至于变成真空中的纸片人。读者看到磨损了的地毯、桥梁的照片、松脱的墙纸(来自伍尔夫早期的小说《夜与日》)时,就和作者达成契约:我相信你笔下的角色是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而且,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当然,物品还有最重要的作用,它以实体来隐喻不可见之物,这里说的当然就是福楼拜笔下那只著名的晴雨表:在《一颗简单的心》中,它躺在钢琴上方,测量出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大气压,而这种压力就如同生之重负一般沉重地压在主角身上,使她一辈子劳劳碌碌却一无所得。
也就是说,小说中的物质实体是具有重量的,同时又是隐喻的、轻盈的,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伍尔夫笔下这颗圆圆的卷心菜,它的重量压低了克拉丽莎天平的一端,又隐喻着她的人生到底和彼得不同,她被牵引到了一个更务实也更日常的世界中。这也才能解释,为何彼得会大骂她是平庸的,而她有时候也觉得彼得“叫人难以忍受,没法相处”——他们在精神气质上,似乎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克拉丽莎在婚后,还是会频繁地想起彼得,这不是说她余情未了,而是说明她的内在矛盾:彼得身上有她可望而不可即的气质,而她对目前的生活是不甘心的。
所以,我常常觉得这部小说是一部“中年之书”。
因为只有中年人才会有强烈的不甘。与年轻人相比,中年人的不甘之痛在于,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翻盘”了,一切基本上都尘埃落定。我时常会和中文系的学生谈及“如果”这个话题:毕业如果不去做中小学老师,最想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提到过“网红”、入殓师、咖啡师、小卖铺老板、自媒体等等。学习中文专业的四年时间其实也并不算长,大有机会从头再来的,也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说,选错专业、爱错人、入错行都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因为沉没成本没那么大。可是对于一个已经投入大半生的中年人来说,日子每过一天就是多一天的积重难返,跟他们谈起推倒重来简直是残忍的。
所以,只剩下了不甘心。你希望走那条路,但是生命的重力却推着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在这条路上花了大半生的时间,回首从前,发现还是意难平。生活中的遭遇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兴趣、偏好、节奏,但却不可能改造一个人天性里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命运的重力。人甚至会参与制造那些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你已经觉得是有问题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还是只能不撒手地一直做下去,这仍是重力的牵引。
总体上,读者在小说中感到的是一种宽容而略带嘲讽的基调,人们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世界里不断折返、试探与碰壁。当克拉丽莎被判定为庸俗的尖酸时刻,伍尔夫又总会加入人物的自哂,克拉丽莎会笑话自己折腾来折腾去是为了什么呢,也会带着不甘期待另一种人生。这种自嘲或不甘的语气,冲淡了尖酸,使得整部小说的气息趋于酸碱平衡:批判终是带着爱意的,沉溺里也总有自我反思,每个人都只能过他注定的生活,没有谁应该遭到轻视;所有人都多少沉沦在自己的苦涩与喜乐中,没有更高级的也没有更低级的。珍惜值得珍惜的,哀悼一切逝去的,这可能是生活自带的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