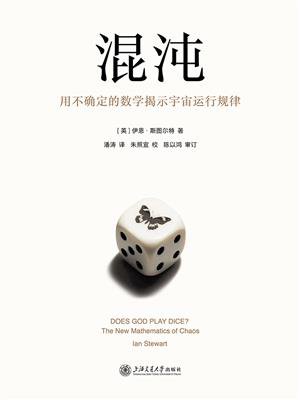荷兰混沌
“气体”一词,是比利时化学家海尔蒙特(Helmont)
 在他1632年的著作《医学精要》(
O rtus M edicinae
)中,特意借与希腊词“混沌”的相似性而发明的。这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选择。
在他1632年的著作《医学精要》(
O rtus M edicinae
)中,特意借与希腊词“混沌”的相似性而发明的。这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选择。
在气体物理学中,无规则性与确定性首次正面交锋。但是在原理上,气体是一些服从精确动力学定律的运动分子的一个纯粹确定性的聚集体。那么,无规则性来自何方呢?
答案——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它被称职的科学家无意间给出,大多数科学家到20世纪80年代初仍在给出——在于 复杂性 。气体的细致运动过于复杂,我们无法把握。
假设你拥有一台仪器,当一定数量的气体分子运动时,它能进行跟踪。这样的仪器并不存在,就算它存在,你必须利用计算机把气体分子运动放慢好几个数量级,以便观察正在发生的情况;姑且假设它存在吧。你会看到些什么?请把注意力集中于一小群分子。它们作短时间的直线运动,然后以你根据分子轨迹的先前几何形态所能预言的方式开始相互弹开。但当你刚要端详运动的模式时,一个新的分子从外面不期而至,与你很有条理的分子群相碰,破坏了这模式。而在你弄清楚新模式之前,又一个分子闯了进来,接着是又一个,又一个……
如果你所看见的全部内容是非常复杂的运动的一小部分,那么整个运动将 呈现 无规则, 呈现 无结构。
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使得社会科学如此棘手的同一个机制。你不能通过分离出一小部分来研究一种活生生的经济,或者一个民族,或者一种思维。你的实验子系统将不断遭受意想不到的、无法控制的外部影响的干扰。甚至在自然科学里,实验方法的大多数日常工作是用来消除外部影响的。百老汇大街闪烁的霓虹灯有效地把夜生活中和下等社会中的人群吸引到脱衣舞夜总会和酒吧中去,但它们严重干扰了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一台敏感的地震仪不仅记录地震,还会记录下在走廊上推车的递茶小姐的脚步。物理学家为消除这种不希望有的影响而大大走向极端。他们把望远镜安置在山顶上而不是曼哈顿的屋顶上,他们把中微子计数器埋藏在地下数英里处而不是放在办公室里。但是社会科学家甚至连这样花钱的自由都没有,他们不得不用统计学方法去模拟或滤去这些外部作用。统计学是一种从复杂性的泥沙中淘取珍贵的秩序的方法。
100年前的科学家就很清楚,确定性系统的性态会以貌似无规则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他们知道它不是 真实的 无规则;它不过是由于信息不完善而 看上去 如此。他们还知道,这一虚假的无规则性只存在于很大、很复杂的系统——具有极多自由度、极多不同的变量、极多分部的系统——之中。这些系统的细致性态将永远处在人类思维能力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