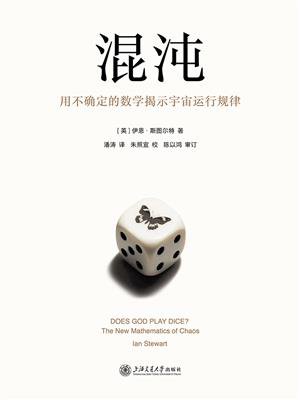钟表世界
以牛顿为顶峰的科学思想革命,导致把宇宙视为某种巨大的机械装置,它的作用“像钟表机构”(我们仍用这个短语——尽管在数字式手表时代这是不合时宜的——来代表可靠性和机械完善性方面的极致)。从这种观点看来,机器最首要的是可以预言,即在相同的条件下将做同样的事情。一名了解机器的性能和它在任一时刻的状态的工程师,原则上能精确地算出所有时间它将做什么。让我们把这个著名而不复杂的问题( 实际上 而不是高度原则上可能的问题)搁置一旁,先看看为什么17、18世纪的科学家们发现他们对于这个充满奇观、令人惊诧的宇宙,却有一种初看起来显得如此贫乏和古板的看法。
牛顿把他的定律提炼成数学方程的形式,这些方程不仅把一些量,而且把这些量的变化率都联系起来。当一个物体在恒定重力作用下自由下落时,它的位置不会保持不变——如果那样的话,它会无依无靠地停留在空中,这显然不可能。物体的速度——位置的变化率——也会改变。物体继续下落时间越长,速度就越快:这就是从高楼坠落比从低楼坠落更危险的缘故。可是,加速度—— 位置的变化率的变化率 ——却是恒定的。我们现在多半能明白,这一动力学规律何以经过这么多世纪才引起注意:只是对于那些对简单性获得新概念的人来说,这条定律才是简单的。
包含变化率的方程叫作 微分 方程。一个量的变化率由它在两个邻近时刻的值之差确定,“微分”一词因此渗入数学:微分学、微商、微分方程等,还有就是单纯的微分。求解不含变化率的代数方程,并不总是易如反掌,正像我们大多数人吃了苦头才知道:求解微分方程更要难上一个数量级。站在20世纪末叶回溯以往,竟有那么多重要的微分方程 能够 十分巧妙地被解出来,这真令人啧啧称奇。数学的一个个分支都由于研究单一而关键的微分方程之需而发展壮大起来。
尽管求解特定的方程尚有技术性困难,可还是能建立一些一般性原理。就目前的讨论而言,主要的原理是:只要已知某一动力学系统所有分量的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则描述这一系统的运动的方程就具有 唯一 解。一辆自行车有五六个基本的运动部件,如果 现在 我们知道每一部件的状况,我们就能预知这辆车从它沿着路面被推开时起到跌入路边沟中为止的运动。推而广之,如果在某一给定时刻,我们对太阳系中物质的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都了如指掌,那么这些粒子所有以后的运动都唯一地被确定下来。
为简单起见,这一陈述假定不存在任何对运动的外部影响。假使把诸多的外部因素都考虑进去,同样得出结论:整个宇宙中物质的每一个粒子在某一给定时刻的位置和速度完全决定它未来的演化。宇宙沿唯一一条预定的动力学轨道演变。
它只能做一件事
。18世纪一位一流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de Laplace)
 (图3)在他的《概率的哲学导论》(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Probabilities
)中以雄辩的口吻写道:
(图3)在他的《概率的哲学导论》(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Probabilities
)中以雄辩的口吻写道:

图3 拉普拉斯在阅读自己的著作《天体力学》( Celestial M echanics )(19世纪平版画)
假使有一位智者在任一给定时刻都洞见所有支配自然界的力和组成自然界的存在物的相互位置,假使这一智者的智慧巨大到足以使自然界的数据得到分析,他就能将宇宙最大的天体和最小的原子的运动统统纳入单一的公式之中:对这样的智者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确定的,未来同过去一样都历历在目。
这是从数学中的简明的唯一性定理得到的一个令人敬畏的陈述。后面我将揭露转变中所含的某种聪明的花招,因为它确实是很强横的;但此刻我们暂时允许这解释成立。在考察类似拉普拉斯这样的陈述时,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科学中盛行的乐观气氛,因为一个接着一个的现象——力、热、波、声、光、磁、电——都是利用同一手法加以控制的。它看上去似乎是对终极真理的突破性进展。 它管用 。于是产生了经典确定论的范式:在没有任何无规则外部输入的情况下,如果方程唯一地规定系统的演化,则系统的性态自始至终唯一地被确定。